■本报记者 倪思洁
近日,著名灵长类动物学家珍·古道尔去世,享年91岁。这位用一生努力与野生动物对话的科学家,让人们重新审视人类与动物之间的关系。她曾说:“唯有理解,才能关心;唯有关心,才能帮助;唯有帮助,才能都被拯救。”
这条哲思,也是很多中国科学家的时空轨迹。李松海20余年倾听着鲸豚的声音,李家堂在恐惧与敬畏中走进蛇的隐秘世界,于秀波以科学视角守护候鸟的驿站,欧阳志云用30多年光阴为大熊猫重构生存版图。他们用科学家的理性与悲悯,在深海、高原、湿地、森林里,与无数生灵对话,让它们被理解、被关心、被帮助、被拯救。
守护,不仅是拯救那些正在消失的生灵,更是对人类文明过度自大的一次校正。这是一条重新出发的回归之路,每一步对我们与它们,都是一次救赎。
李家堂
从小怕蛇,如今很喜欢蛇
作为一名蛇类研究与保护者,中国科学院成都生物研究所研究员李家堂不是天生的“异宠”爱好者。小时候,没见过蛇的李家堂,从老人们讲的故事里,生出了对蛇的恐惧。
2004年秋天,24岁的李家堂第一次走进导师的实验室。推开门的一瞬间,他的汗毛都立起来了。地上爬着蛇,桌上盘着蛇。柜子上、椅子上,目光所及之处,到处都是蛇,活生生的蛇。
他的导师是两栖爬行动物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赵尔宓。李家堂知道,导师实验室里趴着的都是无毒蛇,但蛇的模样仍让他不寒而栗。他壮着胆子走进去,毕竟研究蛇是他自己的选择。
在本科期间,学动物学的李家堂就注意到,蛇类在维持生态平衡和生物多样性稳定方面有重要作用,中国大约有350至400种蛇,其中的30%至40%被列入濒危。“这是个很有意义的研究方向。”他决定报考行业内“大咖”赵尔宓的研究生。
跟导师接受学术训练的5年里,李家堂对蛇的恐惧虽然无法完全消除,却也在一次次野外科学考察中,慢慢得到缓解。
有一次,李家堂在云南景东县的一座山里调查两栖动物,被一只趴在树上的翠绿树蛙吸引了。他紧紧盯住树蛙,轻手轻脚地靠近。就在几乎要捉住树蛙时,余光里隐约出现了一条绿色的“长绳”。李家堂心头一紧、汗毛竖立。他的头顶上方,一条又长又绿的竹叶青蛇,正对着他张开大嘴。一瞬间,李家堂被本能驱使,拔腿就跑,没跑出几步,他又壮着胆子停下来,转身把剧毒的竹叶青蛇装进样本采集箱。
后来,李家堂具备了可以带队“出野外”的能力。他发现,遇到蛇时,自己不仅不恐惧,反而会兴奋。
2015年,李家堂带领学生到青藏高原去找西藏温泉蛇。西藏温泉蛇是世界上分布海拔最高的蛇类之一,无毒,大多生活在海拔3500米以上的区域,是中国特有珍稀保护物种、国家一级保护动物。
李家堂记得,当时天气不好,大家在海拔4000多米的地方艰难地寻找,不少人都出现了头疼、气喘等高原反应。当大家终于找到西藏温泉蛇并成功采到样本时,那一刻的喜悦难以言喻。直到今天,李家堂都记忆犹新。
之后,他带领研究团队跑遍了西藏大大小小的温泉,邂逅了数不清的西藏温泉蛇,也开展了西藏温泉蛇高原极端环境适应与演化机制相关研究。在青藏高原,他最喜欢寻找旁边有溪流的温泉,那里很可能有西藏温泉蛇的踪迹。“温泉可以给它提供热量,溪流可以为它提供鱼、蛙等食物。”
如今,国内外学术界只要提到“西藏温泉蛇”,大概率会想到“李家堂”。他的工作曾得到美国系统生物学家戴维·希利斯等同行专家的高度认可,并获得“中国动物学会青年科技奖”等多项殊荣。
“科学研究要摸清物种多样性的本底,了解生物适应环境的机制。只有掌握了这些之后,才能更好地支撑自然保护区设计,提供政策建议。”李家堂说,随着国家对科研投入加大,如第二次青藏高原科学考察和新疆科学考察等专项的实施,蛇类多样性明显增加,情况开始向好的方向发展。
他的团队里有很多志同道合的年轻人。除了研究西藏温泉蛇,李家堂也带着大家从动物学、基因组学、医学、仿生学等多学科视角,研究蛇类的物种多样性、时空分布格局与演化。
“我团队里清一色的都是从小喜欢蛇的年轻人,他们对蛇有特别深的感情。”李家堂说,他的实验室跟当初他导师的实验室一样,随处可见无毒蛇。为了了解蛇的全生命周期过程,实验室建立了一条“蛇卵孵化—小蛇繁育—成年蛇养护”的全生命周期链。
“我现在还是很喜欢蛇的,我相信你们见了也会很喜欢。等你哪天去我们实验室,给你们看一下!”李家堂笑着说。

世界上分布海拔最高的蛇类西藏温泉蛇。王聿凡/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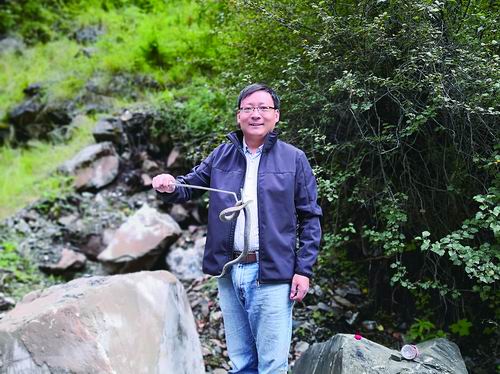
李家堂。受访者供图
李松海
从山村少年到鲸豚守护者
三亚海滩上,一头3米多长的短肢领航鲸搁浅在岸边。中国科学院深海科学与工程研究所(以下简称深海所)研究员李松海和他的同事们把它救回去,放在网箱中照护。几天后,这头鲸还是去世了。
这是李松海几年前遇到的事,但直到今天,回想起这件事,他还是会低头呢喃:“它就这么活生生地在我的眼前死掉了。”
作为鲸豚类动物的研究者和保护者,李松海要经常出海寻找鲸和豚,他遇到过很多让他心碎的画面:有的中华白海豚背鳍被船只螺旋桨划伤,被切成两半或是整个被切掉;有的中华白海豚被圈套住,圈勒进肉里,只要它长大,就逃不脱残疾的命运……
与鲸豚相处的20多年里,作为科研人员的李松海,对鲸豚产生了一种超出职业范畴的感情,就连个人微信名都叫“dolphin”(海豚)。
小时候,李松海生活在江西一个偏远的小山村里。他不知道短肢领航鲸、抹香鲸、蓝鲸有什么区别,也不知道海豚、白鱀豚长什么样子。他只是从父母的口中听说过,“海里有像山一样大的动物”。
后来,少年李松海走出山村,以优异的成绩考入武汉大学,学习微生物专业。命运的转折发生在毕业后。武汉大学紧挨着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以下简称水生所),2002年,李松海毕业时,因为一个偶然的机会,遇到了水生所研究员王丁。当时,王丁正致力于白鱀豚的保护研究。跟着王丁,他见到了那头被人类救护并长期饲养的白鱀豚“明星”——淇淇。那时,他才知道“原来长江里还有这种水生哺乳动物”。
“我很幸运,见过活着的淇淇,就在它去世前几天。”李松海说。
2002年夏天,在人工饲养条件下存活了22年半的淇淇,因高寿自然死亡。紧接着的秋天,李松海成为王丁的研究生,也由此成为鲸豚的守护者。
2007年,李松海博士毕业后,又先后在美国伍兹霍尔海洋研究所、夏威夷大学和新加坡国立大学等科研机构、高校学习和工作。2012年,获悉中国科学院准备在三亚成立一个新的深海研究所时,他立即回国加入,并建立了中国第一个以海洋哺乳动物命名的研究室——海洋哺乳动物与海洋生物声学研究室,以及首个南海鲸类动物资源数据库。
之后很长一段时间,他要么待在实验室里,要么“漂”在海上。
在实验室里,李松海带着团队揭示了齿鲸动物声呐系统的发声与听觉机制,在鲸类环境适应与演化机制、生物声学等领域取得多项成果。他常常会小心翼翼地整理一段段鲸豚录音。当音箱里传出鲸类空灵悠扬的叫声时,他的眼神会变得柔和而专注。那些看似冰冷的数据,把他带进了与远洋深处生灵的无声对话。“每一种鲸豚都有自己独特的‘方言’,它们是非常聪明的生物。”
在海上,李松海带着团队用各种仪器设备追踪鲸豚的踪迹,收集它们的声音。他们在海南西南海域,首次发现了中华白海豚种群。去年,李松海还作为首席科学家参与了短肢领航鲸生存状况考察,并领导团队完成了南海鲸类关键栖息地研究。
海上,触目惊心的一幕幕,有时会让李松海产生一种无力感。“我们不是不想救,是没有能力救。”李松海深知,即便把这些受伤的生命救助上来,给它们治疗,依然无法让鲸豚种群逃离因人类种种生态破坏行为而带来的生存威胁。他知道,这不是一个人、一个团队、一家科研院所甚至一个国家凭一己之力可以做到的事。
“我们面临的最严峻问题,是对这些动物了解得太少。就像中华白海豚,我们最近几年才弄清楚不同地理种群之间的关系,而有些种群可能只剩下十几头。这些基础问题都对保护工作至关重要。”他指出,太平洋东岸、美国近海等地区对鲸类的研究已有几十年积累,而南海和印度洋地区大多数鲸类种群的基本信息几乎一片空白。
谈及目前南海和印度洋鲸类保护面临的最大挑战,李松海坦言,这个区域涉及的大多是发展中国家,甚至是比较贫穷的一些国家和地区,“大多数老百姓还面临温饱问题,谈鲸豚保护,基本上是没有经济基础的”。
如今,除了在实验室和海上,李松海还频繁地出现在各种学术类、动物保护的国际会议,以及媒体上。他希望唤醒更多人,让他们喜爱、理解、守护鲸豚,就像他当初在看过淇淇之后就立志成为鲸豚守护者一样。
“鲸豚类动物是海洋里的哺乳类动物。它们和人类一样恒温,也和人类一样用肺部呼吸、怀胎产子、用乳汁哺育幼儿。尽管体形庞大,但它们很少得癌症。它们的心脏供血能力极强,能承受深海的巨大压力。它们的大脑发达,有复杂的语言系统……”在公开场合,李松海常常如数家珍般地讲述这些,努力激发公众对于鲸豚的关心和重视。
他也期待着有一天,人工智能技术能够帮助人类破解鲸豚的语言密码,实现跨物种交流。“那时候,我们或许能真正听懂它们的声音,理解它们的世界。”

▲被圈套住的中华白海豚宝宝。

▲李松海读研究生期间正在记录江豚的发声。
受访者供图
于秀波
一位科学家成为观鸟爱好者
闲暇时,中国科学院地理与资源研究所研究员于秀波喜欢和妻子丁慧一起去北京奥林匹克森林公园散步。每次,他都会在脖子上挂个望远镜。这是他逛公园的必备工具,也是他与鸟类建立的连接“通道”。
鸟的“灵性”,总是令于秀波动容。在种类繁多的各种鸟中,他最偏爱白鹤。
白鹤,被誉为鸟类界的“明星”,是地球上最古老的物种之一。“太极拳里面有一个招式叫‘白鹤亮翅’,这个姿态很优美。”谈起白鹤,于秀波的眼神变得温柔起来,“作为迁徙的鸟,一个白鹤家庭总会在同一个地方停留,今年在那儿,明年还在那儿,后年还会在那儿,这种鸟很有灵性。”
如今60岁的于秀波,一谈起观鸟,就快乐得像个孩子。他会手舞足蹈地模仿自己在鄱阳湖看到的反嘴鹬:“它的嘴是这样反翘起来的,吃东西是这么左右摆着头,扫着吃的,而且成群结队,队伍特别整齐,连转弯都一起转。啊呀,我开心得不得了。”
当前,像于秀波一样的观鸟爱好者越来越多。这些年,观鸟已经从一项小众的专业爱好,发展成覆盖“银发族”和年轻人的大众休闲活动。
不过,与普通的观鸟爱好者不同,于秀波的本职工作是从科学研究角度开展湿地保护与可持续利用。观鸟,既是他的兴趣,也是他的工作。
2000年,他去澳大利亚考察,发现澳洲朋友在车上摆了3件套——交通图册、观鸟书、望远镜。朋友常常中途停车下来观鸟。他意识到,观鸟是国外非常普遍的活动,鸟也是连接科学与公众、科研与政策的最佳纽带。
“湿地好不好,关键看水鸟。如果湿地保护得好,水鸟的种群数量也会很可观,而且,水鸟更容易引起大家的共鸣。”于秀波说。正因如此,他近年将研究方向聚焦于水鸟及其栖息地保护。他和他的团队成员一年四季都在野外调查鸟类的种群变化等情况,春天是候鸟迁徙季,夏天是候鸟繁殖季,秋天又到了迁徙季,冬天则进入了越冬季。
他们时常带着望远镜和照相机在鄱阳湖、黄河三角洲、辽河口等地调查鸟类。新的观测技术,让他们的工作效率越来越高。以前,研究人员都是靠眼睛来观鸟、数鸟,看不清、数不准的情况时常发生;现在,他们用卫星跟踪器,将带有太阳能电池的芯片绑在鸟的脖子或后背上,每个小时都能定位鸟的行迹。
“最近,我们通过5只背负卫星跟踪器的白鹤,获取了白鹤来回5次迁徙的完整数据,把白鹤的完整迁徙路径弄清楚了。”于秀波笑着说,“它们从俄罗斯苔原带的繁殖地出发,途经蒙古和中国东北的扎龙、辽河口等地,最终抵达鄱阳湖越冬。”
近年来,黄河三角洲成为白鹤重要的越冬地,2023年这里聚集了600多只白鹤。于秀波团队用数据证明了白鹤在鄱阳湖分布的新变化,即白鹤在从自然生境向人工生境转移。
于秀波团队的研究成果为观鸟爱好者们提供了寻鸟线索,反过来,观鸟爱好者们也成为于秀波团队的科研“伙伴”,他喜欢将观鸟爱好者们称为“公民科学家”。于秀波说:“有很多观鸟爱好者认鸟的水平是很高的,中国有1800多种鸟,想都认识还真不容易,是他们教我认识了很多鸟。”
鸟类迁徙等生态学研究,依赖大量的、覆盖面广的数据。在于秀波看来,观鸟爱好者们上传的鸟类数据是“大数据”,科研人员可以通过分析这些数据,为国家在湿地与水鸟保护方面的决策提供支撑。
近年来,随着保护力度加大,一些地方出现了“人鸟冲突”,有时上万只天鹅和大雁飞进藕塘,铺天盖地,大片莲藕很快就被吃完了,让农户欲哭无泪。于秀波发现,观鸟成了缓解“人鸟冲突”的好办法,社区居民可以做“鸟导”获得收入,当地的民宿等相关产业也能得到发展。
作为观鸟爱好者和科学家,于秀波喜欢去中小学给孩子们讲候鸟迁徙、生态保护的科普课。为了吸引更多的年轻人,一向内敛的于秀波常在课堂上热情地唱起“小燕子,穿花衣,年年春天来这里”的童谣。在科普课的结尾,他还不忘鼓励台下那些稚嫩的面孔,因为“教育一代人,就可能解决中国的生态问题”。

于秀波。李运恒/摄

2025年越冬季,鄱阳湖白鹤从自然生境向稻田高密度聚集。于秀波/摄
欧阳志云
守护“国宝”家园的“熊猫伯伯”
“竹子开花啰喂,咪咪躺在妈妈的怀里数星星,星星啊星星多美丽,明天的早餐在哪里?”
1984年,一首火遍全中国的公益歌曲《熊猫咪咪》,唱出了一些忧虑。当时,四川岷山、邛崃山系及九寨沟等地,大熊猫的主要食物——冷箭竹大面积开花、枯死,加之栖息地被人为破坏,大熊猫陷入严重的“粮食”危机。
过去30多年里,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研究员欧阳志云一直在努力守护大熊猫的栖息地。他被很多人称为“熊猫伯伯”。
在《熊猫咪咪》刚“火”起来时,欧阳志云还是湖南农业科学院园艺研究所的一名研究实习员,工作内容与大熊猫毫无关联。1993年,欧阳志云在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获得博士学位。他的博士论文与一种名为“地理信息系统”(GIS)的技术有关。当时,在国内生态研究领域,这是一个小众且前沿的空间分析技术。
同年7月,在一场与生态保护相关的学术会议上,欧阳志云介绍了GIS技术在生态保护上的应用。他的报告当场就吸引了卧龙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以下简称卧龙保护区)副主任张科文的注意。
“你说的这个技术,能不能用来做大熊猫的栖息地评价?”张科文问。“虽然没人做过,但我觉得可以试试!”欧阳志云答。
一个月后,欧阳志云带着设备走进了卧龙保护区,平生第一次看到了大熊猫活动的痕迹:新鲜的粪便、被啃食的竹枝、林间小径上的爪印。这让他觉得很奇妙,“虽然没见到真身,但知道它们就在不远处”。
这次经历开启了欧阳志云与卧龙保护区管理人员和技术团队长达30多年的合作,也让欧阳志云爱上了中国特有的“国宝”动物。
他们在卧龙保护区建立起全球定位系统(GPS)监测站,给“华华”“美美”等4只大熊猫戴上GPS项圈,每隔两三周,下载一次数据并进行分析。他们还研究大熊猫的粪便,探明它们最喜欢吃的竹子种类,并测量森林里竹子和竹笋的生物量,估算栖息地对大熊猫种群的食物承载力。
大熊猫的很多生活习性被慢慢揭开。他们发现,大熊猫属于“早起型”动物,早上6点到8点进入活动高峰,经过漫长的午睡后,又会在傍晚6点到8点活跃起来;每只大熊猫有不同大小的活动范围;它们会避开牧民牧马的区域;它们最爱的竹子除了冷箭竹之外,还有拐棍竹、玉山竹;它们只在有竹林的森林中活动,几乎不去高寒草甸……
基于这些研究成果,他们为保护区提供了一系列管理“秘籍”,其中包括将耕地恢复为竹林,鼓励当地农民种竹子,然后将新鲜的竹子出售给大熊猫繁育中心。“如此一来,大熊猫的‘早餐’解决了,保护区当地的农民也可以通过种植竹子获益。”欧阳志云笑着说。
有了在卧龙保护区的研究经验,欧阳志云团队又将研究范围扩展到全国。他们不只是在守护大熊猫的“早餐”,而是在守护大熊猫的“家”。2021年,我国将73个自然保护地整合,将一些隔离的大熊猫栖息地连接起来,形成了总面积2.2万平方公里的大熊猫国家公园,里面栖息着约1300只大熊猫,占我国野生大熊猫总数的73%。
如今,大熊猫栖息地面积扩大、野生种群数量回升,大熊猫不会再出现“早餐”危机。然而,当年那首《熊猫咪咪》里表达的忧虑,始终萦绕在欧阳志云的心头。
“大熊猫的种群在增长,但还没有完全摆脱危险。根据我们过去10年的数据,大熊猫被隔离成了33个种群,互相之间难以交流,影响着种群安全。有些小种群只有两三只大熊猫,面临着灭绝的风险。”欧阳志云说。
这种危机意识,让年过60的欧阳志云依然一年两三趟地往山里跑。“当年,我们的前辈靠着大熊猫的脚印和粪便做调查;现在,我们有卫星遥感、无人机巡护、物联网、分子生物学等各种先进技术,数据也更精准。但是,无论技术如何进步,野外考察始终不可替代。科研人员必须到现场去,实地观测、分析。”欧阳志云说。
在欧阳志云看来,野生动物保护,说到底是要管理人类的行为,正如《熊猫咪咪》结尾唱的那样,“请让我来帮助你,就像帮助我自己,请让我去关心你,就像关心我们自己”。这句歌词唱出了欧阳志云的心声。栖息地保护之路还长,而守护仍需继续。
(本报见习记者江庆龄对本文亦有贡献)

欧阳志云(后排右三)与他的研究伙伴们。 受访者供图
《中国科学报》 (2025-10-16 第4版 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