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
放弃讲席教授,选择“7年一考核”!她把“任性”之举当寻常 |
|
|
文|《中国科学报》记者孙滔
今年9月25日,美国霍华德·休斯医学研究所(HHMI)珍妮莉亚研究园区的高级组长王萌团队迈出了长寿研究的一大步。他们在Science以研究论文形式发表了揭示秀丽隐杆线虫长寿跨代遗传机制的研究,发现了体细胞如何把环境信号传达给生殖细胞继而传递给后代的秘密。
这项研究是一场持久战,持续了五六年。这段时间里,她作了一个不寻常的决定:从无需考核、资源充足的贝勒医学院RobertC.Fyfe讲席教授、HHMI研究员,转而在2022年成为珍妮莉亚研究园的高级组长——一个每7年需要考核一次的岗位。很多人不解,究竟是怎样的信念让她作出这样的选择。
就像对马拉松长跑的热爱一样,这位研究长寿与衰老的科学家给出的答案是,她要跑出自己的节奏。
 王萌
王萌
?
6年磨一剑的分子侦探故事
谈到秀丽隐杆线虫的时候,王萌会嘴角上扬,眼睛里放出光来,那盈盈笑意给人春风扑面的观感。
这种模式生物是长度约1毫米、全身透明的虫子。在这个小生物的帮助下,她致力于解开衰老与长寿的谜团。
他们这项Science研究始于一个意外发现。
一直以来,对于跨代遗传,科学家关注的是生殖系统,但很多跨代遗传的现象发生跟环境改变息息相关。当环境改变时,尤其是发生和饮食相关的饥饿反应时,最先强烈感受变化的是体细胞,而生殖系统应是受到高度保护的。王萌经常感到困惑,最先对饥饿产生反应的躯体与负责遗传的生殖系统之间存在隔离,这时候跨代遗传是如何发生的呢?尤其是像长寿信号这样的躯体获得性特征,是如何跨代传递给后代的?
在王萌实验室2015年的另一篇Science论文研究中,他们发现了溶酶体中存在一种调控脂肪代谢的酶,其在肠道中的高表达能显著延长线虫寿命。在把转了这种溶酶体脂酶基因的长寿线虫和野生型线虫杂交后,她的博士后张庆昊意外发现,其后代在缺失转基因的前提下仍然表现出跨代长寿优势,寿命延长多达18%。
这个意外发现让他们敏锐地猜测,在亲代线虫中,这种溶酶体脂酶触发的信号可以诱导“长寿表观记忆”的形成。
他们最终解开了谜团:当线虫处于易长寿的环境里,它的肠道会生成一种叫组蛋白HIS-71的信号使者。这个小使者能突破肠道和生殖系统之间的关卡,钻进卵母细胞,然后在里面“写下”一条“长寿指令”——这条指令不会改变基因本身,却能像记忆一样传给后代,所以即使后代乃至于跨代中没有长寿基因,也能活得更久。
这是一个分子侦探故事,细节清晰、逻辑完整,同时也是一场持久战。王萌和张庆昊都想把这个谜团彻底解开。尤其是张庆昊,在王萌实验室搬到珍妮莉亚研究园后,为了不影响研究进程,他留守在贝勒医学院长达两年多。在好奇心的驱动下,他们摸索了很多不同的方法,最终成功打通了这个信号通路的上下游,把谜底真正挖掘了出来。
他们的工作有点“慢”,但在王萌这里,耐心就是捷径。王萌说,“我们很多工作都是这样,像是解谜。很多线索摆在那里,但你不知道谜底,不知道它的完整图景。你不断地发掘新的证据,推倒曾经做过的假设,从各个方向摸索,到最后你就发现,所有的线索突然指向了同一个方向。那时就像到了过山车的顶点一样,所有的证据带着你越来越快地接近谜底。这时你会发现,原来你之前所做的努力都是有意义的。”
这种“慢”也给了王萌不一样的回馈。一次在美国杜克大学作完学术报告后,有学生听众告诉她,她实验室的文章曾经被当作研究范文,供学生学习怎么做实验设计、怎么把机理讲完整。王萌很有感触,原来自己的工作不仅仅给予读者知识,还能帮助新手建立一种做研究的风格,影响他们从事科学的态度。
在自己的实验室,王萌很庆幸自己有志同道合的学生和博士后。张庆昊就是其中之一。审稿人没有提到的问题,他想到了,他就会设计实验,主动去挖掘、求证。
如今,张庆昊即将入职浙江大学基础医学院。王萌在朋友圈感慨说:“有趣的实验现象需要一双慧眼的留意,机制才会被抽茧剥丝地挖掘出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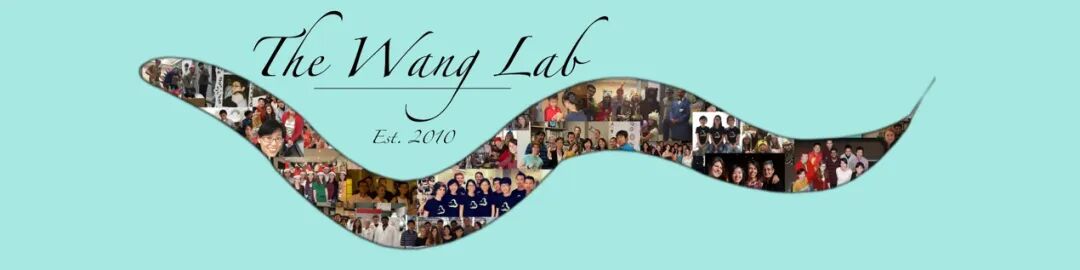 王萌实验室的网站设计,图片集呈线虫形状
王萌实验室的网站设计,图片集呈线虫形状
?
始于意外的长寿研究
王萌的科研生涯,从一开始就与长寿和衰老结下不解之缘。
在美国罗切斯特大学读博期间,她通过果蝇的一个突变基因发现了一条调节长寿的新信号通路。那也是一项由意外发现引发的研究。
那是研究生轮转期间,王萌在做一个和应激反应有关的果蝇课题。当整理果蝇瓶子的时候,她发现在正常果蝇已经全部寿终正寝的时候,某个基因突变的果蝇还有很多存活,并且看起来很健康。于是,她就在轮转结束后,把这个现象告诉了导师。尽管这并非他们课题组本来的研究方向,但他们在商量后就打算深入研究这个突变体。
最终,他们解释了应激信号通路是如何和营养信号通路相互作用,从而对长寿产生影响的。两篇相关研究论文分别发表在Developmental Cell和Cell。
多年后,她认识到,这些工作之所以成为可能,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是遇到了很好的导师。这样的导师能够给她足够的空间,让她在新的方向上自由发展。如今,她也把这种风气带到了自己的实验室。
从哈佛医学院的博士后工作开始,她的研究模式生物从果蝇转向线虫。为何会有这个转变?王萌的解释是,线虫是全体透明的,可以在荧光标记后直接观察到大分子的生理变化;线虫的寿命很短,只有两三周,可以极大缩短研究周期;而且线虫是很好的高通量研究模型,可以在短时间内同时筛选很多条件,处理和分析大量数据。她的博士后导师是2024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的获得者、哈佛医学院遗传学教授GaryRuvkun,也是一位研究兴趣广泛、鼓励自由创新的导师。
不过,线虫研究的短板也是显而易见的。因为距离转化医学很远,他们获取项目支持的难度远远超过了以小鼠和人类为研究对象的方向。尽管线虫研究并不需要过多的经费,但他们还是会遇到困境。她有时也会跟团队成员开玩笑:“哪天实验室开不下去了,我就想办法弄一台显微镜回家,把车库改装了,在里面继续做实验。”
说这句话的时候,她没想到,后来因为新冠疫情,实验室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处于封闭状态。她不得不弄了一台显微镜,搬回家里继续做实验。回想起这段不易,她有点佩服自己:“即便在那种情况下,我想的仍是怎么能运一台显微镜回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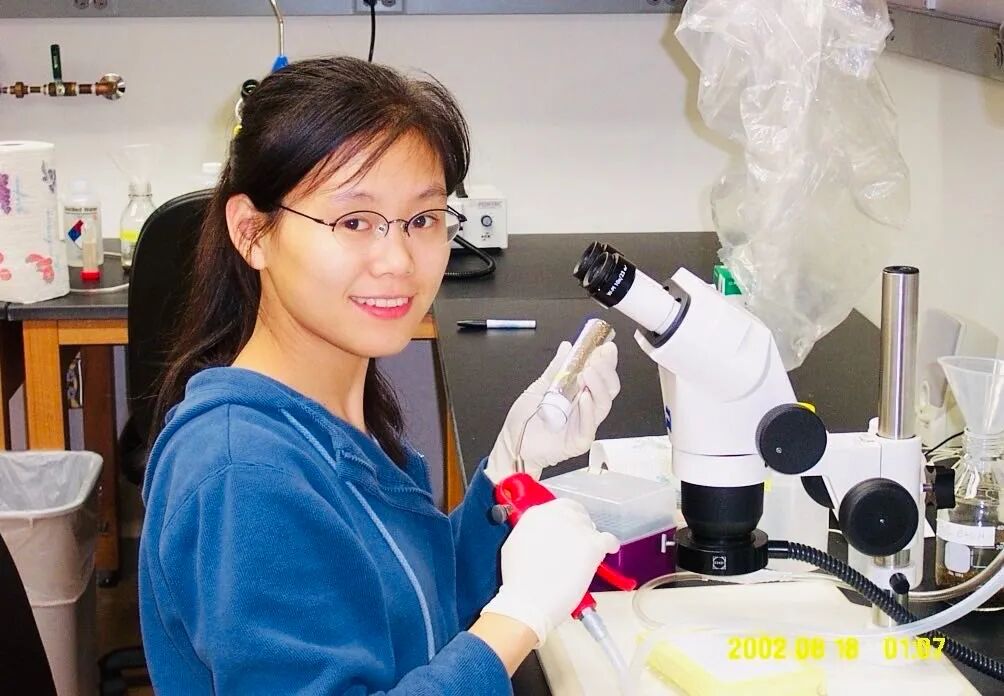 2002年,研究生一年级时的王萌
2002年,研究生一年级时的王萌
?
显微镜下的“无人区”
平时有一点时间,王萌总喜欢能在实验室做点什么,哪怕只是把转基因线虫从一个盘子转移到另一个盘子,或者给这些线虫拍照。即使是一个小时的实验操作,她也会特别满足。
对此,儿子小时候很不理解,问她:“妈妈,你这么多工作,不累吗?为什么不能多陪我玩会?”她用了一个无比简单的回答,让小朋友瞬间就理解了:“妈妈在实验室做实验,就跟你在家里玩乐高一样啊。”
王萌深知自己的热爱所在。因为现在外出开会、讲座比较多,她经常遗憾自己不能有很多时间呆在实验室做研究。
王萌的科研天赋,早在研究生期间就已显露——她尤其擅长找到新的突破点。她的第一篇果蝇研究论文,聚焦“细胞自主调节”(即细胞自身内部的调节活动),她的导师也建议她继续沿着这个方向深入。但她觉得寿命调节是个体反应,应该会有不同的器官参与,是不是有未知的细胞非自主调节机制?如果把果蝇的各种器官,尤其是大脑,解剖出来研究会怎么样呢?
为验证这个想法,她开始摸索一项尚无人涉足的“手术”:在显微镜下用镊子解剖果蝇成虫的完整大脑。成年果蝇仅2.5毫米,其大脑只有针尖那么大,她必须一只手固定果蝇头部,另一只手迅速剥离脑壳——动作稍慢或力度过重,果蝇的大脑形态就会改变,柔软的皮层就可能被破坏。
解剖完果蝇,她还要继续染色观察,完工就是半夜了。当她看到玻璃皿中漂浮的果蝇大脑显示出染色结果的时候,她难以抑制兴奋。这个研究也就是那篇发表在Cell上论文的核心内容。
她的导师也很震惊,直夸王萌的手太稳了,完成了一件其他人从未有过的操作。王萌说,自从她毕业后,导师的课题组里就再也没有谁能做这个“手术”了。
很多年以后,在王萌多次学术报告之后的交流中,还有人提及,“原来那篇Cell论文是你做的呀,当年就觉得是很漂亮的工作!”
王萌的科研天赋,不仅在于稳定的双手,更在于她乐于琢磨并改进现有方法。
读博期间,当系里买了一台新仪器,她就会是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她还会摸索新的方法,分享给他人。博士后期间,她需要定量检测特定基因的表达水平,实验指南要求用数万条线虫提取核酸,操作繁琐、时间漫长,但王萌却觉得有优化空间。她花了一周反复摸索,最终把线虫数量从数万条降到数百条,还验证了方法的可靠性——后来,她的新方法不仅在自己课题组沿用,还被其它实验室借鉴。
这并非多么巨大的创新,但能帮助很多人。
直到今天,她的课题组仍然在做这样的努力,包括张庆昊在这篇Science研究中,也巧妙开拓了多项方法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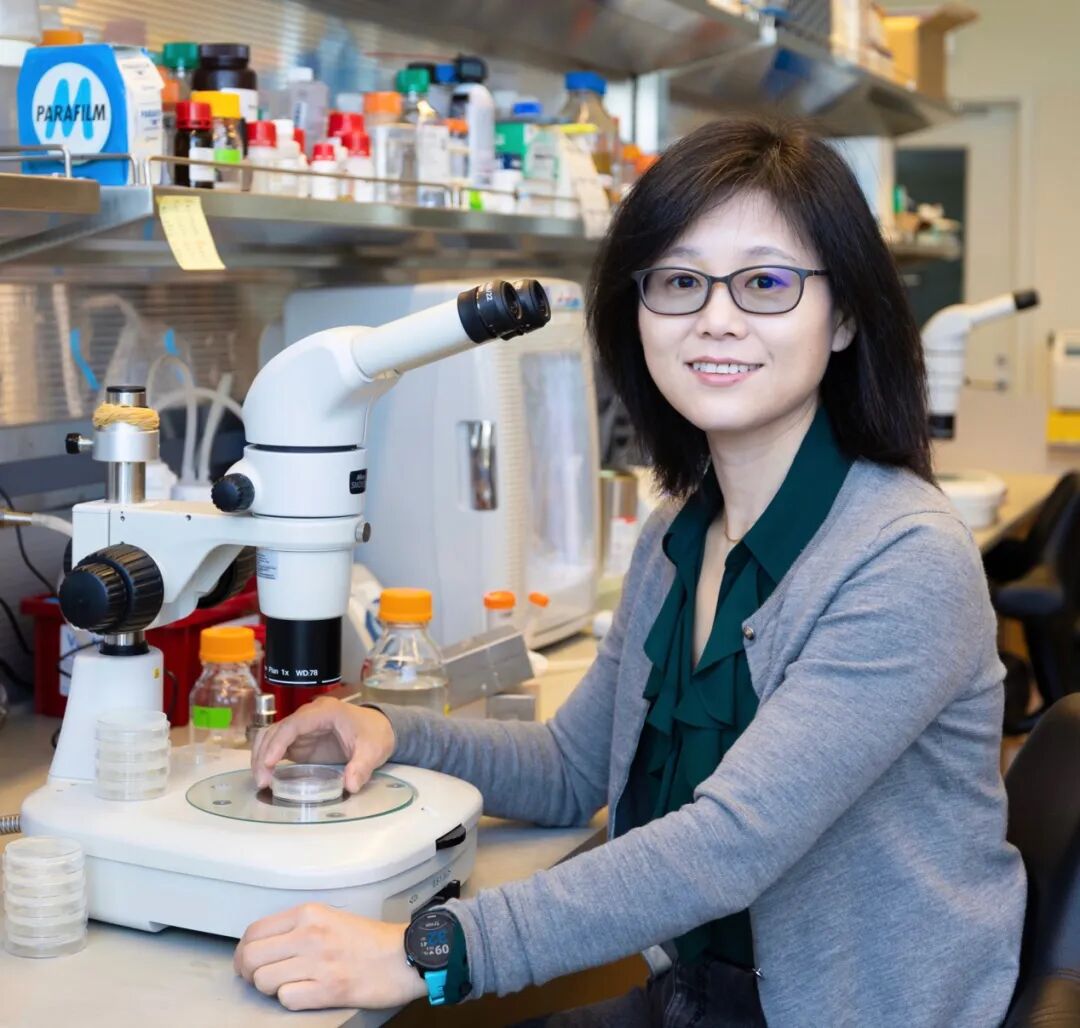 2025年,王萌在实验室
2025年,王萌在实验室
?
一切为纯粹科研
落子无悔,王萌一直相信这句话。
她很早就打算学生物学专业,因为当年在石家庄一中读初中时,她遇到了一位出色的生物老师。那位刚刚从大学毕业的老师教了她很多知识,有些是课本上都没有出现的。她意识到,这些正是她想做的事情。
高三时,王萌有一个保送清华的机会,但她拒绝了——因为那不是她想读的专业。这让她的父母很是着急,万一高考考不好呢?班主任也劝她,生物系毕业出路很窄。王萌的答复是不后悔。她还是去参加了高考,最终在1997年被北大生物系录取。
对于这些异于常人的决定,她只是觉得当年自己的心比较大。
她另外一件心大的事情,则是跳槽到珍妮莉亚研究园。
其实早在2018年,王萌就成为了HHMI研究员,但她还是决定在2022年全职加入珍妮莉亚研究园。珍妮莉亚研究园有她更渴望的环境。这里的研究氛围很纯粹,科研人员不用甚至也不被允许去申请政府机构的基金;珍妮莉亚研究园提供所有的支持。她终于得到解放,可以把更多的时间投入到实验室中来。
不仅如此,珍妮莉亚研究园还很重视开发新实验方法的工作,有着非常友好的多学科交叉环境。这也是吸引王萌的地方。
至于她对长寿与衰老研究的执着,除了科研本身的吸引力,还藏着原生家庭的温暖印记,她的奶奶和外婆都是高寿老人。尤其是她的奶奶,活到了100岁。去世前几周体检时,医生还在惊讶老人的心脏像是50多岁人的心脏。她们也都是无疾而终。
王萌就想,若能把长寿的秘密揭示出来,就可以让更多人享受到这样的人生,而不仅仅属于像她的奶奶和外婆那样少数“中彩票”的幸运儿。
其实,如今王萌对长寿和衰老主题的兴趣,已经远远超出了家庭成员的影响,“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什么别的事情比科学发现更有趣”。
跑出自己的节奏
王萌的科研动力早已不再是发表,而是为了把问题弄清楚。
她在作学术报告时也不再展示已发表论文的期刊,尽管她拥有不少顶刊论文。每当王萌在外边作完报告,就会有学生或博士后来问她:“您的论文发表的期刊很好,为什么不展示出来呢?”
王萌会告诉他们,报告中给出了PubMed数据库的文献编号或者论文的DOI编号,“如果你想了解我们的工作的话,它能让你更快找到这些文献”。
这并不是王萌的个人原创,而是她所在的HHMI的一贯主张,后者甚至要求来作报告的人都要如此操作。
在HHMI,一直鼓励成员能够及时将其研究成果在预印本公开分享。最近,该机构的评审工作都开始以预印本为依据开展了,这也省了王萌每次屏蔽论文目标发表期刊的麻烦,“对我的最大影响就是,终于不用再心疼发文章时的出版费了”。
王萌太认同这样的规定了。科学家的工作本不应该因为研究人、小鼠抑或是线虫而分高低,也不应该因为发表在哪个级别的刊物而分贵贱。但现实是,研究线虫的发表文章确实要难一些。
她认同HHMI的倡议,要让科学回归科学,而非顶刊崇拜,希望其他人逐渐接受这样的理念和做法。
发Science论文已是寻常事,王萌反而对于有人在小红书上介绍这项最新研究很激动。读到那个“我命由我不由天,但可能由爷爷午餐”的帖子,她在朋友圈写道:“为了看自己文章的报道,专门下载了小红书,不得不说这报道写得真是生动有趣啊!”
想到这个研究涉及的是卵母细胞,她不无调侃地说道:“'姥姥午餐'可能更准确些。”
 王萌在今年的休斯敦马拉松赛场上
王萌在今年的休斯敦马拉松赛场上
?
王萌还是一位马拉松爱好者。2022年,她在休斯敦马拉松实现了个人突破,Personal Best(个人最好成绩)是3小时34分——这一成绩成功达标波士顿马拉松的参赛资格,而参加波士顿马拉松正是全球跑者梦寐以求的顶级荣誉之一。
在长跑的赛道上,她从不追随配速员,只想奔跑在自己的节奏里;在科研的赛道上,她同样如此。
她说:“如果总是看着别人,你可能会失去自己。就像跑马拉松,你只要心中有自己的目标,把握住自己的节奏,做到享受过程就可以了。”
特别声明:本文转载仅仅是出于传播信息的需要,并不意味着代表本网站观点或证实其内容的真实性;如其他媒体、网站或个人从本网站转载使用,须保留本网站注明的“来源”,并自负版权等法律责任;作者如果不希望被转载或者联系转载稿费等事宜,请与我们接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