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① 夏欢进行古蛋白采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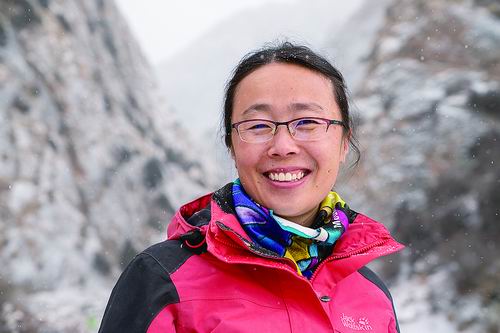
② 张东菊在野外。

③ 张东菊团队成员王建进行动物考古学分析。受访者供图
■本报记者 叶满山 通讯员 曲倩倩
时至今日,兰州大学资源环境学院教授张东菊都忘不了,她所在团队研究的一件古人类下颌骨化石被确定为丹尼索瓦人化石时,内心涌起的激动之情——她漂亮地完成了多年前导师、中国科学院院士陈发虎交给自己的任务。
2019年,由陈发虎领导的兰州大学环境考古团队牵头在《自然》发表了夏河人下颌骨化石的研究成果。该化石将史前人类在青藏高原活动的最早时间从距今约4万年前推至距今至少16万年,首次从考古学上验证了丹尼索瓦人曾生活在东亚地区的假说。
作为一种目前基本可以确认曾广泛分布于东亚地区的古人类,丹尼索瓦人已成为我国考古学领域的一个重要名词。但很多人并未注意到,发现这一成果的团队并非来自国内著名考古强校,而是在地球科学研究方面实力雄厚的兰州大学。
这支根植于兰州大学地理学的环境考古团队,成员来自考古学、地理学、地质学、生物学等多个学科。然而,就是这样一群“跨界”的老师,却带领学生发现了尘封16万年的丹尼索瓦人化石。
跨界起点:考古学到地理学的跨越
在很多人的印象中,考古学往往与田野挖掘、古墓探秘联系在一起。然而在兰州大学资源环境学院,这种场景却被各类先进的实验室、精密的仪器所取代。在这里,传统观念与现代科技形成鲜明对比,甚至让人觉得有些“不协调”。
对于这种“不协调”,团队成员、兰州大学资源环境学院教授杨晓燕很理解。在她看来,他们就是要站在不同学科的角度解读考古发掘出来的各种材料。对以人地关系为核心的地理学而言,就是将目光投向更广阔的天地和更遥远的过往——人类与自然环境之间的“爱恨情仇”。
这就是“环境考古”。
“环境考古的核心在于探讨过去的人地关系,即人类如何适应、利用和改造自然环境,以及这些环境变化如何反作用于人类社会。”杨晓燕告诉《中国科学报》,环境考古更侧重于通过遗存解读人类与环境的互动历史。
很显然,这是从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这两个传统学科中生长出的新学科分支。它在兰大“萌芽”的时间并不长——上世纪90年代,陈发虎在兰大地理系开设环境考古研究方向,并培养该方向的硕士研究生。
彼时,国内考古学仍以历史学框架下的文化序列建构和器物类型分析为主导,研究集中在遗址时代、器物谱系和文化分期上,难以回答人类活动与自然环境协同演化的深层机制问题。在此背景下,一些地理学和地质学领域科学家开始推动中国环境考古研究。陈发虎凭借其自然地理学背景,敏锐意识到了这一新动向。
只不过,当时在兰州大学庞大的校内科研体系中,陈发虎团队关注人地关系研究的只有寥寥数人;而在千里之外的河北,正上高中的张东菊还在为大学梦伏案苦读。
2000年高考,张东菊考入山东大学,并意外被调剂到考古学专业。这让对考古几乎没啥概念的她始料未及。她猜测,这个专业可能像那些玄幻电视剧一样“有意思”。
事实与想象稍有偏差——考古学并不“玄幻”,但同样充满吸引力。于是,她从零开始学习考古学,踏上了这条全新道路。
只不过,在这条路上,张东菊的探索从一开始就有些“不守规矩”。
“大三时,我经历了考古实习。”据她回忆,那时,每位同学要各自负责一个5×5平方米的探方发掘。正是在这次发掘过程中,她第一次体会到了地理学的重要性。
“我发现土层的形成和变化记录了古代自然环境的信息,这些信息对于解读埋藏其中的考古遗存至关重要。”但当时的张东菊对地球科学知之甚少,这让她意识到,要想在考古学领域有所建树,必须补充地球科学知识。
这次实习坚定了张东菊从事跨学科研究的信念。随着相关研究兴趣的增长,获得保研资格的她,开始寻找能提供这种研究环境的学校和导师。巧合的是,借助当时兰州大学与山东大学的一个合作项目,她了解到陈发虎团队在环境考古领域的探索。“这让我看到了跨学科研究的可能性。”
正是这种对学科交叉的渴望,驱使张东菊作出了一个大胆选择——从考古学转向地理学。
初识环境考古:一场跨学科的邂逅
从黄河下游的济南到黄河上游的兰州;从刚刚摸到了一点“门道”的考古学,到几乎完全陌生的地理学,张东菊的这场“逆流”让很多人不理解。
“兰州大学有悠久的地球科学研究历史和雄厚基础,这为环境考古学的发展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我希望通过跨学科研究,更全面地揭示古人类与自然环境间的相互作用关系。”她解释说。
不过,张东菊也有一些“不理解”,这是导师陈发虎带来的。
“刚到兰州大学,陈老师就交给我一个极具挑战性的课题:探讨‘现代人起源和扩散’这个学术界未解之谜。”她说。
这个课题一度让张东菊陷入了深深的迷茫——要解决问题,人类化石、石器等研究材料以及相关专业技术等的支撑必不可少,而作为考古学专业的学生,所有材料都要从零积累,相关技术也要从零学起。这意味着她不但要走出校园寻找遗址,还要不断摸索合适的研究方法。
这正是陈发虎希望看到的。
事实上,从当初那个关注人地关系研究的小团队诞生之初,学科交叉的基因就已深植于团队的发展进程中。在这里,地理学、考古学、地质学、生物学等多学科深度融合,环境考古学科作为新兴研究方向逐步形成,这一切都需要初来乍到的张东菊快速适应。
除学科方面外,张东菊固有的文科思维模式也给她带来不少困扰,甚至因此被导师批评“思想保守”。上学期间,陈发虎花费了大量精力改变她的想法和理念。
从文科到理科,思维方式和写文章的习惯都存在巨大差异。
以写文章为例,受文科思维影响的张东菊写作速度较慢,倾向于先积累知识和想法,在保证观点正确前,不轻易动笔。陈发虎却认为,科研本就是一个进步的过程,在当前阶段,若没有更好的解释,及时发表阶段性研究成果对国内外同行也会有启发,待有新认知时再作更新。
此外,相比于可借助导师手把手指导而快速进步的传统学科研究生,张东菊只能像无头苍蝇一样四处碰壁。
“挑战确实不少。”她感慨道,“从纯粹的文科背景转向理科,需要补充大量地球科学和生物学知识;当时的兰大也没有专门的环境考古研究方向,我需要在全新环境中摸索前行。”
幸运的是,导师给了她很大的支持和自由,使她能自由探索方法解决问题。在此过程中,张东菊通过广泛阅读文献、参加讲座和研讨会,逐渐构建起自己的知识体系。
在张东菊于“碰壁”中不断成长的那些年,兰大环境考古学科也在快速发展,而促使这种成长的仍是不同学科间的碰撞与融合。
2007年,陈发虎指导的第一个考古学背景的环境考古方向博士生毕业;两年后,兰州大学西部环境与气候变化研究院成立,西部环境教育部重点实验室环境考古分支实验室建设完成。2015年,兰州大学资源环境学院和西部环境与气候变化研究院实施合并重组,推动地学与考古学交叉研究进入新阶段。
此后,该团队陆续获批多个科研平台。这些平台的接力建设持续强化了其环境考古领域的学科优势和研究特色。
“年代测定离不开第四纪地质学,骨骼形态分析离不开人类学和动物考古学,石器分析离不开考古学,古蛋白解析离不开分子生物学技术,这些分析在我们团队和实验室都能实现。”张东菊说。
人才培养:宽口径、厚基础、跨学科
伴随着学科的快速发展,张东菊完成了博士论文研究,并在此期间以访问学者的身份先后赴美国、德国学习。2010年,她毕业后选择留在导师的团队,成为了一名老师。
或许是自己的科研经历有着太多“跨越”,初为人师的张东菊很注意对学生跨学科能力的培养。正如她在受访时所说,“我希望能培养既具备扎实考古学基础又掌握地球科学等自然科学知识和方法的复合型人才”。
杨晓燕也告诉记者,团队鼓励学生广泛涉猎不同学科的知识,培养他们的跨学科思维和创新能力。“在课程设置上,我们注重文科与理科的融合,让学生既学习考古学、历史学等人文社科课程,也学习地球科学、生物学等自然科学课程。”
“团队设计了一套多学科融合的课程体系。”团队成员夏欢介绍说,在这套体系中,学生不仅要学习考古学、地球科学、生物学等基础课程,还要参与各种实践项目和国际合作。例如,通过参与遗址发掘项目,学生可以亲身体验地层学和考古学的实际操作;通过参与国际合作项目,学生可以与国际学者共同探索环境考古的新领域。
夏欢正是这一培养体系的鲜活例证。
作为陈发虎和张东菊共同指导的博士,夏欢本科攻读的是自然地理学,研究生阶段则将环境考古作为研究方向。最终,她在古蛋白质组学领域形成独特优势,其研究成果已成功应用于多个研究项目,并获得了业内广泛的引用与参考。
“对于我们这个涉及多学科交叉的领域,单一学科很难真正解决问题,只有对所涉及学科都有深刻认识,才能有机融合多学科的研究结果,讲出完美的‘故事’。”如今已经成为教授的夏欢说。
为了讲好这些“故事”,该团队每年野外工作时间长达3~5个月,发掘工作都由师生亲手完成。“我们要自己去发掘自己研究的样品,这样才能清楚它的出土情况,明白它能解决什么考古学问题,然后在实验室利用自然科学手段进行分析,这样对数据的解释才会有据可依,不会脱离考古学背景。”杨晓燕说。
在从事科研工作的同时,团队成员还利用自身学术资源和人脉关系,为学生争取实践项目和合作机会。借此,学生可以参与团队的大型科研项目,负责数据采集和分析工作;也可以参与国际合作项目,与国外学者共同开展研究。这些实践机会不仅提升了学生的专业能力,也增强了他们的团队协作和沟通能力。
学术氛围:鼓励创新的生态环境
如果说,对于学生的跨学科培养是培育一株幼苗的话,那么包裹在幼苗周围的“营养液”,则是团队内部开放包容的学术氛围。
“良好的学术氛围对于跨学科研究至关重要。”杨晓燕表示,团队特别注重营造开放、包容、创新的学术氛围。
对此,团队成员、兰州大学资源环境学院教授董广辉解释道,团队鼓励学生提出不同的观点和想法,尊重每个人的学术兴趣和研究方向,同时注重培养学生的批判性思维和创新能力,鼓励他们勇于挑战传统观念和方法。
“为营造这种氛围,我们定期举行学术研讨会和讲座,邀请国内外知名学者来校交流;我们还鼓励学生参加国际学术会议和合作项目,拓宽他们的学术视野和交流能力。”他说。
在这方面,让博士生李源新印象最深刻的是团队的每周例行组会。
“组会上,不管是博士生、硕士生,还是刚入师门的本科生,都可以畅所欲言,提出质疑或建议。”李源新告诉《中国科学报》,不管是谁汇报,张东菊都会随时询问“大家有没有听懂”,这种鼓励提问和讨论的方式营造了良好的学习环境,即使学生被问得“语塞”,也不会受到批评。
对此,张东菊解释说:“我现在问学生的问题越多,他们懂得就越多,功底就越扎实,他们毕业答辩时就会越从容。”
从陈发虎播下的环境考古种子,到如今在丹尼索瓦人研究、高原农牧业传播、古人类的高海拔适应机制等领域结出的硕果,如果将兰州大学环境考古团队比作一位寒窗苦读多年的学生,在张东菊的眼中,这名有了如此成绩的“学生”,是否可以“从容答辩”了呢?
张东菊的回答意味深长:“成果代表了过去,也是新的起点,未来真正的挑战在于如何让交叉学科‘活’下去、‘长’起来。”
她告诉《中国科学报》,当前环境考古研究方向在多个高校已陆续成长起来,均呈现出多学科交叉融合、国际合作深化及服务国家战略的特征。
具体而言,传统考古学强校通过新加入的地质学手段辅助环境考古研究,以地质与地理学科为优势学科的部分院校则依靠自身优势,通过构建跨学科团队、搭建国际合作平台等方式,推动环境考古从区域特色研究向全球学术引领跨越。
“环境考古正在突破传统考古学‘就物论物’的局限,将研究视野扩展至人类活动与自然环境的动态互动。”张东菊表示,这一范式转型也推动考古学从“文化史研究”向“社会过程研究”转变。
比如,张东菊带领团队在青藏高原开展了大量考古调查与发掘,他们不只想重建古人类向高原扩散的时空过程,更希望理解这背后的机制,特别是不同人群对高海拔环境适应的机制。去年,他们在《自然》发表了丹尼索瓦人在高原上对多样性动物资源进行充分利用的研究成果,这是回答丹尼索瓦人如何适应高海拔环境问题的重要进展。
在这一过程中,交叉学科团队的重要性愈加凸显。
张东菊表示,任何一个学科团队的成长都会经历风雨,交叉学科团队要想稳健发展,关键在于搭建“营养丰富”的生态平台——既要有如陈发虎这样兼具多学科经验和国际视野的带头人,也要有专门的协同办公空间与实验平台,让不同背景的人才及时交流、无缝合作。
“交叉学科的核心是‘人’,没有包容的政策和多元的人才池,再好的想法也会枯萎。”杨晓燕说。
值得一提的是,当前环境考古作为考古学与地球科学、环境科学等学科的交叉领域,已在国内形成较为系统的研究框架,并打破传统考古学的局限,让考古学在理科学院中焕发出新的生机。
“如今,考古学早已摆脱了单纯的文科研究范式,与多学科深度融合,形成了一种全新的研究范式。”杨晓燕说,这不仅拓宽了考古学的研究视野,还为解决传统考古学难题提供了新思路。
“从这个角度看,考古学已经不再是一个‘冷门’专业了。”张东菊笑着说。

兰州大学资源环境学院师生在考古遗址发掘现场。受访者供图
《中国科学报》 (2025-08-19 第4版 高教聚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