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个正在研究鸟的生态学家,郑诗璐坦言自己曾经爬山很“菜”,也曾是个观鸟“小白”。
可她从没想过“摆烂”。毕竟,野外那么好玩,鸟儿那么可爱。体力不好,可以坚持爬山;对于不熟悉的植物或鸟类物种,就去不断认识、学习。
这期间,郑诗璐还邂逅了标本研究。
最近,她开启了忙碌的新学期。不同于往年,这次她不再是学生,而是以厦门大学环境与生态学院副教授的崭新身份,踏入校园,继续与标本对话。由她主持的鸟类野外调查项目,也即将开始。
郑诗璐说,在学习与科研的初期,可能会发现自己在某些方面暂时很“菜”。但“菜”不要紧,只要不断学习就好。只要有热爱和努力,一定能找到自己喜欢的、适合自己的研究之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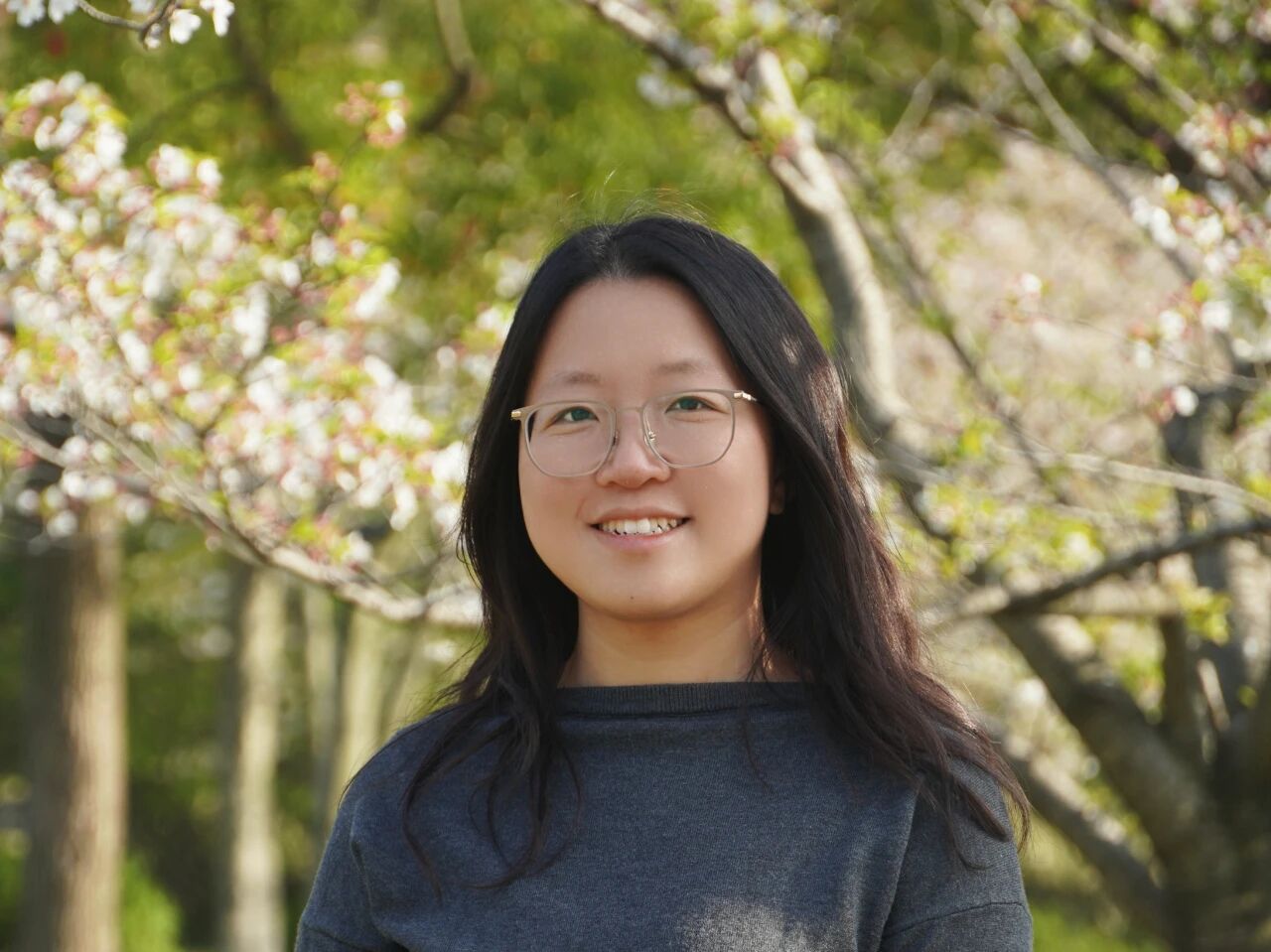 郑诗璐
郑诗璐
?
1 用标本数据做研究
郑诗璐研究鸟是从博后阶段才开始的。
2021年的夏天,郑诗璐成为复旦大学的“准”博后。她一边等待手续办理,一边随导师来到中国科学院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帮课题组做采样工作。在这个生机勃勃的西南边陲小岛上,她开始琢磨自己的课题。
她的博士课题与植物的种内性状变异有关,开启博士后工作后,她便想探索动物性状的变化。
过去的研究发现,由于栖息地保护得当或物种扩散等因素,物种数持续增加,尤其是一些大型鸟类出现频率的提升,使得群落的平均体形和功能多样性随时间增加。然而,这些研究大多没有考虑一点:物种本身也会对环境的变化有响应。
比如,不少鸟类的体形如今逐渐缩小。郑诗璐不禁好奇,这类物种内的性状变化,在更广泛的群落中会产生怎样的影响?
回答这样的生态学问题至关重要。在全球变化的背景下,生物多样性保护和生态系统管理,必须有科学的指导。
该从哪里获得长时间尺度上动物的性状记录?起初,郑诗璐想整合已发表的文献中不同物种体形变化数据,但很多文献没有直接公开数据,即使有,信息也很杂很碎。
她想到了标本数据。标本的收集时间通常横跨几十年甚至上百年,可以直观体现物种性状的变化轨迹。
郑诗璐从标本数据库VertNet中筛选了来自北美博物馆中548个物种的8万份鸟类标本,试图回答体形、翅长等性状的变化会在更大的群落层面带来哪些影响。
她用标本的性状构建模型,将北美持续50年的鸟类群落调查报告中相应物种的观测时间坐标信息代入模型,推测群落的功能多样性。
郑诗璐解释,可以想象在一个三维空间中,548个物种是548个点,不同的物种由于性状的差别,会以一定距离围成一个空间。这个空间的大小,就可以用来衡量功能多样性。
郑诗璐的研究第一次将种内性状变异加入分析,得出与过去截然不同的结论——即群落的平均体形其实呈缩小趋势。而体形不断变小的鸟类个体扩展了群落的功能空间体积,使群落的功能多样性增加幅度更大。
这样的结果说明,如果不考虑物种本身的性状变化,可能会低估群落变化的真实幅度。这项研究最近发表于《当代生物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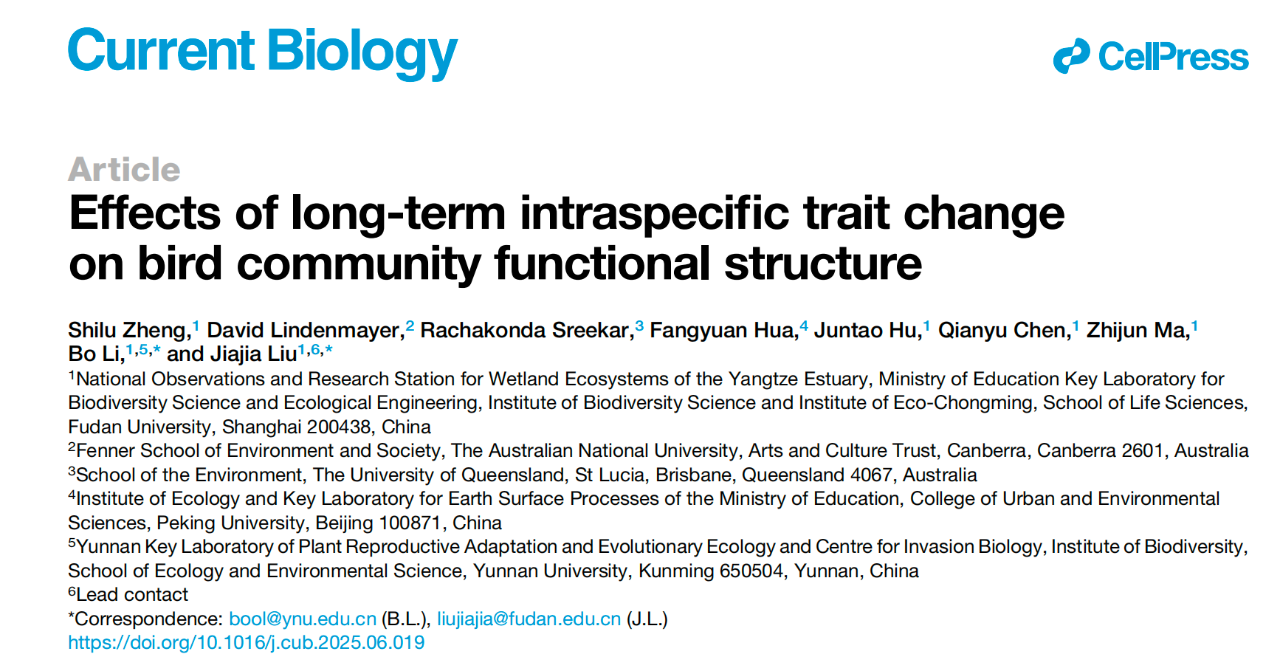 郑诗璐等发表论文截图
郑诗璐等发表论文截图
?
2 建立国内的信息库
这项研究中关键的数据来源是VertNet,它是郑诗璐在翻阅文献期间关注到的网站。这是一个全球博物馆标本数据库,囊括了许多脊椎动物标本的“电子档案”。
对于参观自然博物馆的大多数游客来说,他们或许不清楚,在陈列着栩栩如生、姿态各异的动物标本的展厅背后,还有一个庞大的“仓库”,那里有更多标本静静躺在抽屉中。
这些标本叫做“假剥制标本”。虽然不被展出,但它们大多记录着采集时间、地点与物种鉴定信息。VertNet不仅收录这些信息,还记录有动物标本的体形等性状。
这正是郑诗璐梦寐以求的数据。
虽然VertNet汇集了足够全面的标本信息,然而数据的格式并非绝对统一。许多性状信息挤在一个单元格里,需要人工逐一核查、区分。上万条的鸟类标本数据,需要郑诗璐逐字核实、梳理。
这期间,她得以“云”参观世界著名的自然博物馆的标本馆藏,足不出户就逛了美国哈佛大学的比较动物学博物馆、康奈尔大学脊椎动物博物馆、佛罗里达自然历史博物馆……
而她也意识到一个问题。VertNet虽然收录了全球许多地区的标本数据,但唯独没有中国标本的数据。我国的鸟类标本收藏体量并不小,虽有部分博物馆正在做标本图像数据化的工作,但这些记录通常不会细化到每个个体的性状。
郑诗璐决定唤醒沉睡在抽屉中的宝贵信息,为分析我国鸟类在漫长时间里发生的变化创造机会。在整理Vertnet数据的间隙,她开始和国内的标本馆合作。
郑诗璐先从身边开始,她联系了复旦大学的祖嘉生物博物馆。这里有标本世家“标本唐”积累的雄厚馆藏,其中最“老”的鸟,可追溯到1877年。
郑诗璐召集了志愿者,依次测量馆藏的3000余件鸟类标本。之后,上海自然博物馆也支持了她的计划,将近1万件鸟类标本的性状信息完成数字化。
 郑诗璐(右一)在上海自然博物馆临时库房培训志愿者
郑诗璐(右一)在上海自然博物馆临时库房培训志愿者
?
具体来说,他们会用清晰的表格记录标本标签上的采集时间与地点,再测量标本体长、头长、喙长、翅长、尾长等信息。在安静的库房中,郑诗璐被标本与纸箱包围。在不赶进度的情况下,她会一边测量,一边上网查查手中物种的拉丁学名,对比标本和它们在自然环境中的姿态。
“这项工作的时间和人工成本很高,但希望在不久的将来,能够完成这一项艰巨但意义深远的工作,建立我国鸟类的历史标本性状数据库,留下一份可以追溯的时空印记。”郑诗璐告诉《中国科学报》。
 在复旦大学祖嘉博物馆测量标本
在复旦大学祖嘉博物馆测量标本
?
3 写写好玩的研究
郑诗璐是四川成都人,她儿时的记忆里,与泥土、小动物的亲密接触不算多,但作为一个从小看着自然纪录片长大的孩子,她萌生了对生物学科的兴趣。
高考后,郑诗璐被录取至浙江大学竺可桢学院。她选择了生命科学这个好玩的专业。
在西澳大利亚大学读博期间,郑诗璐经历过一阵迷茫。有段时间,她整日坐在电脑前,处理叶片扫描信息。在进行数据分析前,需要做大量这种重复性整理工作,既枯燥又耗时,短期还看不到结果。
后来她回想,这其实是做科研的常态。但值得一提的是,那时,本科期间认识的师兄给了她一个建议:找一些自己认为有趣的论文,并用通俗又有趣的语言写下来,发在公众号上。做这件事不追求阅读量与传播效果,只是写给自己。
2018年年底,第一篇科普小文诞生了。郑诗璐陆续搜罗了几十个好玩的研究,她曾写过《会读心的山羊》《蜂巢中的城市秘密》《人类活动影响鲸鱼的耳屎》……
让爸爸妈妈也能看懂,是她的标准。
两年过去,这些阅读与写作填补了有些枯燥的时光。更难得的是,通过梳理、书写论文故事的脉络,郑诗璐发现,自己似乎对“如何写好研究故事,让别人愿意读下去论文?”有了更清晰的认识。
后来,郑诗璐申请到复旦大学教授刘佳佳的课题组做博士后。她对生物与自然的喜爱,没有局限在某一个生物类群上,她想回答更广尺度的生态学问题。
 郑诗璐与刘佳佳在新疆出野外
郑诗璐与刘佳佳在新疆出野外
?
在刘佳佳课题组,她参与了许多好玩的研究。比如,他们曾分析宋画里的鸟类多样性、从古诗词中一窥江豚过去在中国的分布、研究古树保护现状等等。
最近,郑诗璐开设了一个新的公众号——XMUBirdLab。她打算让今年招收的学生也尝试同样的事,找一些自己感兴趣的论文,并用自己的语言解释。学生们日常中的自然观察与所思所想,也可以在这个写作平台自由地记录。
“希望学生们不会觉得很讨厌吧。毕竟又多了一个任务。”她笑道。
4 和“大佬”比不了,那就不断学习
扎在标本馆里给鸟类标本“量身高”之余,郑诗璐也期待在自然中与鸟儿相遇。在上海做博后期间,她与朋友们组队参加了几次上海市的观鸟活动。
“我们小队有点‘菜’,成绩一般是中游的水平,和大佬比不了。”但在郑诗璐看来,他们也不需要和观鸟大佬比较。得以目睹小鸟的一举一动,就是观鸟最大的快乐,这样的快乐没有尽头。
在今年的一个观鸟比赛上,她和小伙伴们在一个池塘边蹲了很久,看几只白头鹎喝水看得入迷,腿都麻了,她们都毫无察觉。2024年的观鸟比赛中,郑诗璐还难得见到了几乎与树枝融为一体的夜鹰……这样迷人的瞬间还有很多。
郑诗璐说,自己没有精湛的观鸟技巧,是个抱着学习态度参加观鸟活动的“小白”。“但鸟儿真的很可爱,我观鸟不厉害,那暂时先研究标本嘛!”
如今,郑诗璐加入了厦门大学环境与生态学院的滨海湿地群落生态学科研团队。她在继续推进国内鸟类标本测量的同时,还会开展滨海湿地水鸟的调查工作。对她来说,“数据本身的意义,只有去实地观察、调查,才能知道真实的世界在发生什么”。
其实,在郑诗璐的博士阶段,最初参与到野外调查工作的她感到自己特别“菜”,和其他同学相比,她爬山很慢。但随着课题开展,在野外磨砺了两三年的她发现,一直坚持爬山的自己,比刚开始时轻松了很多。
出野外渐渐成为一种享受,总能给予她灵感与治愈。这也是她做生态学研究的初心。
郑诗璐的选择,也有很多缘分在其中。
大四时,郑诗璐曾在美国佛罗里达大学交流,当时的指导老师Robert Holt是一位理论生态学领域的“大牛”。
郑诗璐初到异国,英语磕磕巴巴,但Robert老爷爷对仍在读本科的她格外耐心。他带她旁听研究生的课程,借给她专业书籍,还带她去买了人生中第一个双筒望远镜,教她如何观察鸟,把她领入观鸟的世界。
 郑诗璐的第一个双筒望远镜和观鸟比赛的纪念品
郑诗璐的第一个双筒望远镜和观鸟比赛的纪念品
?
Robert还会手把手教她做分析,带她看数据,尤其会细究那些在模型趋势之外的数据点所蕴藏的故事。也是从那时开始,郑诗璐开始理解模型分析的意义,看到了数据的魅力。
做博后期间的那几项“支线研究”中,郑诗璐并不是一作,但她参与了自己最擅长的一环——数据建模与统计分析。
郑诗璐曾看过一个说法,大意是,有越来越多“fancy”的模型出现,但我们不是必须掌握那些看起来复杂、厉害的模型。把简单的模型用好,也可以做出重要的成果。
最新的那篇论文里,郑诗璐使用了混合线性模型。“是不是一听就觉得还挺简单的?”她腼腆地笑了。
成为新晋博导的郑诗璐,最近时常想起佛罗里达州那个温和的冬天,还有Robert温暖的关照。她告诉自己,如果学生就像当年的自己,很“新手”还缺乏信心,那就给他们尽可能多的鼓励,帮助他们学会独立学习的方法,找到研究中的乐趣,找到适合自己的研究。
相关论文信息:
https://doi.org/10.1016/j.cub.2025.06.019
文中图片均由受访者提供
特别声明:本文转载仅仅是出于传播信息的需要,并不意味着代表本网站观点或证实其内容的真实性;如其他媒体、网站或个人从本网站转载使用,须保留本网站注明的“来源”,并自负版权等法律责任;作者如果不希望被转载或者联系转载稿费等事宜,请与我们接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