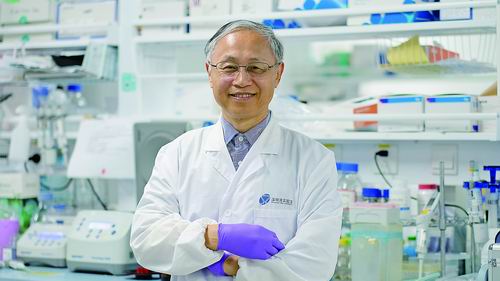
周耀旗在深圳湾实验室。受访者供图
■本报记者 田瑞颖
2021年,周耀旗回国加入深圳湾实验室,出任系统与物理生物学研究所副所长。彼时的他,怀揣着一个梦想:将前沿研究转化成实际药物,最终造福全球患者。次年9月,靶向RNA(核糖核酸)小分子药物企业——砺博生物在深圳成立,周耀旗是创始人之一。
近日,砺博生物完成近亿元Pre-A轮融资。在周耀旗看来,清晰的差异化技术路径、可验证的里程碑达成能力,以及高度契合中国创新药发展阶段的战略定位,是企业能够在资本寒冬中逆势突围的重要原因。
深圳湾实验室主任、深圳医学科学院院长颜宁发来祝贺:“我们始终致力于构建‘从实验室到临床’的完整创新链条,砺博生物的案例正是这一理念结出的硕果。”
创业的想法开始萌生
周耀旗是一位把深度学习方法应用到蛋白质主链结构预测中的科学家。对他而言,创业并非一时兴起,而是30多年的技术积累、10多年的等待与蓄力。
1984年从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化学物理系本科毕业后,周耀旗前往美国纽约石溪大学攻读计算统计力学博士学位,随后在诺贝尔奖得主、美国哈佛大学教授马丁·卡普拉斯的课题组从事博士后研究,在此期间,他的研究逐渐转向计算生物学。正式工作以来,他先后任教于美国布法罗大学、印第安纳大学,不断拓展用计算手段探索生命奥秘的学术边界。
在印第安纳大学,分子生物学专家詹剑的出现,为一直在寻找实验合作伙伴验证计算预测的周耀旗打开了新的局面。后来,詹剑成为砺博生物首席执行官。
后来,两人前往澳大利亚格里菲斯大学,开创了计算与实验融合的“干湿结合”研究模式。在那里,两人的研究重心逐步转向RNA结构与功能。他们还与人工智能(AI)专家、格里菲斯大学教授Kuldip Paliwal合作,成为全球最早将深度学习技术应用于蛋白质主链和RNA二级结构预测的团队之一。
从那时起,创建新药研发企业的想法就在两人心中生根发芽。
周耀旗解释说,当前,新药开发面临大量“难成药靶点”久攻不下、成本高昂的困境。传统的新药研发类似于“锁和钥匙”的匹配机制,需要在蛋白质表面找到合适的结合位点——“锁眼”,药物分子——“钥匙”才能发挥作用。然而,许多导致重大疾病的“坏蛋白质”表面找不到合适的“锁眼”,导致传统小分子药物难以结合,研发投入巨大却屡屡失败。
周耀旗团队的技术路线独辟蹊径,绕过蛋白质本身,直接靶向指导蛋白质生成的“源头指令”——RNA。“我们结合AI预测来快速定位关键区域,再通过高效的湿实验平台进行验证和筛选,从而精准找到能破坏‘错误指令’的小分子化合物,从源头阻止疾病蛋白的产生。”周耀旗说。
这种“计算指导实验、实验反馈优化计算”的闭环研发策略,不仅拓展了小分子可成药靶点的范围,还压缩了传统靶点发现和分子发现中“假设—验证”的周期,为曾经被认为“无药可靶”的疾病带来新的治疗希望。
耐心等待最佳时机
之后,周耀旗没有急于启动创业,而是耐心等待最佳时机。他说:“生物医药研发是一条漫长且资源密集的道路,仅凭科学家自身的热情和有限的资金难以持续。”
转机出现在周耀旗回国加入深圳湾实验室。创新工场和红杉中国很快找到周耀旗,对靶向RNA三级结构创新理念表现出浓厚兴趣,希望与他共同开辟这一新赛道。
这时候,周耀旗意识到时机成熟了。
与此同时,詹剑也全职回国。他们的理念还吸引了药物化学专家、后来的砺博生物首席技术官方超。此前,方超已积累了10多年的小分子药物研发经验。在美国生物医药公司Arrakis Therapeutics任职期间,方超牵头构建了RNA靶向小分子(rSMs)平台,为公司争取超过3亿美元的合作预付款和资金。
2022年,3位科学家合作创立砺博生物,他们在计算、生物、化学领域的研究背景让这家初创企业能够无缝衔接地从靶点发现推进到先导化合物优化。
周耀旗在接受《中国科学报》采访时坦言,由于大家研究侧重点不同,融合初期也曾面临“共同语言”的挑战。经过多次深入讨论,团队逐渐建立了基于共同目标的沟通框架,让计算预测更贴近实验验证需求,也让化合物设计更早纳入临床转化考量。
砺博生物在成立后两年多时间里,搭建并验证了包括靶点发现和分子发现在内的技术平台。周耀旗介绍,在中枢神经系统疾病方面,一条管线已完成主要临床前研究,即将启动中美双报;在肿瘤领域,两条管线已接近确定临床前候选化合物,相关分子在体内外药效、选择性及初步安全性等方面均表现优异。
詹剑告诉《中国科学报》:“砺博生物预计到2026年进入临床阶段,这意味着我们有望用3年时间完成从实验室概念到临床候选药物的关键跃迁。”
与资本成为伙伴
在周耀旗看来,企业的顺利发展离不开投资人的深度支持,双方形成了真正的“伙伴”关系。
创新工场和红杉中国作为首轮投资人,除提供财务支持外,还在战略规划、公司治理、团队搭建和后续融资等方面提供了高价值指导和资源引入。“它们扮演了真正的‘天使’和合伙人的角色。”周耀旗说。
近日,砺博生物完成的近亿元Pre-A轮融资由天士力资本和磐霖资本共同领投。“本轮融资将加速我们将科学理念转化为真正惠及患者的药物。”周耀旗表示。
相比那些“算法漂亮、数据薄弱”的AI企业,砺博生物在融资时就已通过内部管线高效产出多个活性与选择性俱佳的候选化合物,并获得了关键的体内外实验验证数据。“这证明了平台不仅前沿而且可用,对于投资人而言是最直接的风险降低信号。”周耀旗说。
此外,科研团队构建的高技术壁垒,以及精准把握“颠覆性技术”与“未满足临床或市场需求”的交汇点,也是获得资本青睐的重要因素。
很多初创科技企业都曾遭遇“死亡谷”挑战。对此,周耀旗表示,他们非但没有陷入其中,反而加速跨越了这一阶段。“跨越‘死亡谷’不是被动求生,而是依靠系统方法主动突破。”
对此,他分享了三个策略:第一,企业从创立之初就设定了以关键数据产出为目标、有时间节点、可衡量的路径,并且按时保质保量达成目标。第二,打造“平台技术”这一护城河,不押注单一产品,而是建立能持续产出候选化合物的、AI赋能的RNA靶向小分子发现平台,显著增强抗风险能力,让投资者看到可持续的价值创造。第三,与资本构建“伙伴”关系而非简单融资,“聪明资本”可以帮助企业更精准地规避研发陷阱,加速价值实现。
在平衡科研探索与投资收益方面,詹剑介绍了团队的做法:将研发管线分为两类。“收益导向型”管线靶点验证度较高、机制相对成熟,风险较低;“探索导向型”管线则包含前沿靶点或全新作用机制,虽然周期长、风险高,但一旦成功将带来颠覆性回报。
詹剑认为,这两类管线并不矛盾,前者支持企业“行稳”,后者支持企业“致远”。在实际操作中,“收益导向型”管线致力于快速推进到临床验证阶段,支持企业价值逐级提升;而“探索导向型”管线则着眼于追求长期、爆炸性、难以颠覆的优势,为企业长期价值增长准备驱动引擎。
创业以来,周耀旗团队深切感受到国内创新环境的蓬勃活力、各级政府对生物医药的大力扶持、灵活的人才政策与监管沟通机制,以及兼具成本与灵活性优势的合同研究组织。
“我们始终相信,用小分子靶向RNA不是难以实现的概念,而是正在发生的治疗革命。我们希望做这场革命的推动者与实践者,为全球患者带来新的希望。”周耀旗说。
《中国科学报》 (2025-09-22 第4版 科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