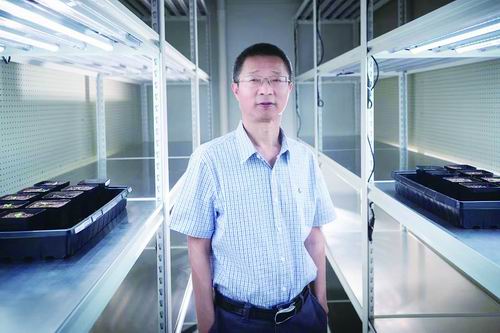
柴继杰
■本报记者 田瑞颖
从造纸厂的助理工程师,到研究植物免疫的世界顶尖科学家……提到江湖上关于他的 “传奇”故事,有着辽宁人特有的幽默感的柴继杰,眼睛笑成一弯新月。
不久前,作为中国首位获亚历山大·冯·洪堡教席-国际研究奖(以下简称洪堡教席奖)的学者,57岁的柴继杰全职回国加入西湖大学,紧接着就获得了2023“未来科学大奖——生命科学奖”。
近20年来,柴继杰一直在寻找植物抗病“自救”的命运之钥。柴继杰在结构生物领域真正“上道”是在31岁,他作出前往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做博士后的决定。在那里,施一公刚刚组建团队,他成为施一公的第一个博士后。如今,柴继杰培养的学生不少也已成为学科带头人。
初心:回报国家
《中国科学报》:2017年,你作为中国首位获得洪堡教席奖的学者,前往德国科隆大学和马克斯·普朗克植物育种研究所继续相关研究。研究期满后,你为什么选择回国?
柴继杰:我到德国的第二年就很想回国。我之前在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和清华大学工作过。从软环境来说,国外的科研人员对科学的专注度可能相对好一些。但从硬件上讲,国外不一定就比国内好,支持力度也未必比国内大。中国无论是基础研究还是“卡脖子”技术,都在下决心要做起来。
语言也是我想回国的一个重要原因。德国以德语为主,语言不通让我非常沮丧。马克斯·普朗克植物育种研究所要好得多,可以用英语交流。但科隆大学说德语的人还是很多,听到大家用德语交流,感觉自己是局外人。
《中国科学报》:此次全职回国,你是否带着更大的计划?
柴继杰:不知道能不能说“更大”。我们在过去几十年里有很多积累,主要聚焦于基础研究,解决一些科学问题。我们一方面会继续做植物免疫的基础研究,另一方面也想做更“接地气”的事,希望能把植物免疫知识应用于实践。
具体来说,比如植物病害是造成植物减产最重要的一个因素,我们希望利用积累的知识使植物自身能更有效地防护病虫害,减少化肥的施用,同时也希望做其他尝试,如让化肥兼具农药的作用等。
国家对我们大力支持,我希望能对国家和社会有所回报,这是我的初心,也是最朴素的想法。
《中国科学报》:回国后你受聘为西湖大学讲席教授,这所学校最吸引你的地方是什么?
柴继杰:大学最重要的目的之一是传播知识和积累知识。西湖大学就是要把教学和科研作为最重要的事,让其他都为之服务。
在教学上,西湖大学不仅看重硕士、博士教育,还非常重视本科生教育。在科研上,无论是后勤服务还是其他方面,学校都全力支持,让我们能全身心投入到科研中。同时,学校还提供了一个宽松的学术环境,让我们有充分的空间自由进行探索。
逆袭:靠兴趣和坚持
《中国科学报》:1983年,你考入大连轻工业学院制浆造纸专业,毕业后被分配到丹东鸭绿江造纸厂。你为什么选择制浆造纸专业,并在4年后跨专业读石油化工科学研究院的硕士?
柴继杰:我是1983年上的大学,那时候信息不像今天这样发达,只能凭报纸上的招生简章填报志愿。当时我报了听起来挺“高大上”的轻工业机械专业,但最后被调剂到制浆造纸专业。
大学毕业后,我被分配到造纸厂,当时每个月工资是66元。后来我觉得不是特别适合工厂的环境,很想继续上学,就选择了当时比较热门的石油化工专业。
《中国科学报》:硕士毕业后,你前往北京协和医科大学药物研究所读博士,跨专业读蛋白质晶体学。你是怎么进入这一领域的?
柴继杰:读硕士的时候,我还没有真正找准想做什么,只感觉对合成比较感兴趣,所以就报考了有机合成专业的博士,最后成绩也不错。但当时老师说这个专业光有理论不行,还得有实验基础,所以就把我推荐给另一位研究晶体学的老师。我便开始研究蛋白质晶体学,这恰好是结构生物学的重要基础课程。
《中国科学报》:你3年就取得了博士学位,为什么之后又前往在普林斯顿大学刚组建团队的施一公那里,并成为他的第一个博士后?
柴继杰:上世纪90年代,国内外在学术上的差距还很大,大家都很想出国学习。施老师的实验室虽然刚成立一年多,但成果已经很不错了。博士后期间,我确实学到了很多东西。尤其是刚加入时,实验室只有我和一个研究生,施老师那会儿完全是手把手教我,可以说是得到了他的真传。
《中国科学报》:听说在施一公的团队里,你是出了名的“不按常规出牌”,而“天马行空”的想法又总能帮助你突破研究瓶颈。你如何拥有如此活跃的思维?
柴继杰:可能是我当时没有在“圈”里,没有所谓的知识背景,这反而让我以一种不同的方式思考问题。如果我一直受这个领域的影响,也许会被一些固定思维框住。
我还有一种思维习惯,就是遇到任何事情都喜欢思考,不是人云亦云,或者盲目相信文献。做研究要有批判性思维。
我经常跟学生说,要学会实验思变。如果实验卡在某个地方,继续反复做肯定不行,只有变化才可能产生不同结果。我当时在普林斯顿大学做博士后时,就有一个关于表达蛋白的课题,通常情况下这种实验的温度都是22℃~24℃。有一天我突发奇想,想试试温度放到16℃会怎么样,一个很小的变化最后确实产生了巨大的差别。
实际上很多开创性研究,不一定有天翻地覆的变化,只要思路稍微变一下,就像捅破窗户纸一样简单。
《中国科学报》:你从在造纸厂工作到成为结构生物学领军学者,被很多人视之为励志的传奇人生。你认为这段逆袭之路,最重要的是什么?
柴继杰:我觉得有两点特别重要——兴趣和坚持。
其实我们很早就开始做NLR受体(胞内核苷酸结合和富含亮氨酸重复序列受体)了,做了近20年才出成果。但植物调控免疫有两类重要的受体,我们在另一类PRR受体(膜表面模式识别受体)上也一直做得不错,有很多重要成果。这能够给人以信心,从而获得足够的支持让我们保持初始的兴趣。
坚持自己认定的东西,这对科研是非常重要的。不光是我,我的学生也是这样。我对有些课题最初也是没有什么信心,但是学生一直在坚持,最后真就做出来了。
科研:独立思考和善于交流
《中国科学报》:成为导师后,你培养了很多优秀人才,不少已成为相关领域的学科带头人。在培养人才上,有什么独特的方法吗?
柴继杰:如果说在这方面我有功劳的话,可能就是与他们交流得很多。不光是在他们的学生期间,包括以后参加工作、做独立PI,我们的交流也很多。
《中国科学报》:你有很多学生,也有很多自己的科研工作。跟大家保持高频的交流,可能要占据你很多时间。
柴继杰:我的优势是非常专注。因为我没有什么行政职务,不需要花任何时间去做其他事,可以完全集中在研究上,这对我做科研非常有利。而且我也非常愿意跟学生交流。如果这种交流能帮助或提供一些想法给他们,尤其某个想法真有用时,我自己也是一种享受。
《中国科学报》:对于学生选择导师,你有什么建议?
柴继杰:首先要对所做的研究有兴趣,另外导师的科研思维应该活跃。能做出东西不仅仅在于你发篇什么样的文章,更重要的是在这个过程中你学会了什么。
《中国科学报》:相比国外学生,中国学生有什么独特的优势以及待改进之处?
柴继杰:中国人刻苦努力,这是我们最大也是最明显的特点。但是受传统文化影响,我们会更加内敛,在很多问题上可能不善于发表自己的意见,也不是非常积极主动,这也许是需要改进的地方。
《中国科学报》:对于新组建的植物免疫信号传导实验室,你希望让学生在这里得到怎样的锻炼?
柴继杰:对于研究生来说,有过硬的技术是基本的,同时要有独立思考问题的能力,初步具备独立科研的能力。我不在的时候,他们也能解决很多具体问题。博士后期间的要求会更高。不仅要有独立解决问题的能力,更重要的是学会提出问题,假如将来你成立一个实验室,要清楚自己想做什么。
《中国科学报》 (2023-09-07 第4版 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