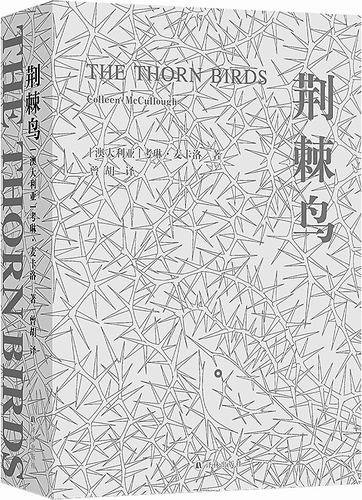
《荆棘鸟》,[澳大利亚]考琳·麦卡洛著,曾胡译,译林出版社2021年3月出版,定价:68元
■帅雯霖
一
20年后再读《荆棘鸟》依然被它感动。
只不过这次重新定义拉尔夫与梅吉的爱情。少年时感动的只是有情人不能成眷属的悲剧,而这次的感动是,这么坚韧的爱情,时间摧垮不了,任何人也摧垮不了。成年人的爱情就是克制和隐忍,而不一定是得到和相守。
与其说《荆棘鸟》是家世小说,毋宁说《荆棘鸟》是深刻阐释传统意义上的爱情的人性小说。它阐述了人性与欲望、隐忍与牺牲之间的关系。当人的野心、欲望与爱欲相冲突时,又不得不被生活掣肘,只能心有不甘地接受、隐忍,而无法做到不顾一切地按个人欲望去生活。
这也是一本复线小说,和《红楼梦》一样埋藏着几条线,同时并行。小说有三条线,一条是克利里家族一家三代从新西兰到澳大利亚奋斗的背景线,是大背景,所有人物都在这个大背景下演绎着他们的悲欢离合;另一条线是这个家族三代女人的爱情组线,妈妈菲奥娜、女儿梅吉、外孙女朱丝婷;第三条线是本书的主线,那就是梅吉与拉尔夫的“禁忌之爱”,这是主轴,大背景线和三代女人的爱情组线,都是为了这条主线。
《荆棘鸟》写的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生活背景下的爱与生命,尽管那时的爱情现在看来是传统的,但这种“传统”的爱情反而是永恒的主题,爱情的本身就是爱,而不是利益和得到;爱是一种忍耐和等待,成年人的爱就是一种忍受而不是占有,是一种即使得不到也要坚持下去的爱。更多的是生活在镣铐下生存的人。这样的人是大众的、平凡的,所以读时才会有悲悯的情怀。在哪个时代这都是爱情的底色和生活的本来面目。
这是本纯正的爱情小说。小说几位主人公把一生只对一份爱负责当成一种信仰。菲奥娜把一生献祭给了初恋;父亲帕迪把一生的爱给了母亲菲奥娜;梅吉把一生献给与拉尔夫的“禁忌之恋”;而朱丝婷把内心的爱给了弟弟戴恩,所幸最后她逃出生天……
小说男主拉尔夫是一个无法享受凡俗之爱的教士,他曾立下献身上帝的永恒誓约,但他终究是个人,是个男人。外表完美的拉尔夫有着世俗的野心,他渴望到达教廷的中心,披上主教的红色法衣,得到梦寐以求的权力。野心本身无所谓对与错,他渴望接近上帝。直到他遇见了梅吉,从此,他彷徨无助,苦不堪言,他在上帝之爱和人类之爱之间苦苦挣扎,他既背叛了上帝,又辜负了爱情。但最终他还是选择站在了上帝和权力一边,放弃了梅吉,但他的内心却一直没有放下这人间之爱。
而女主梅吉就是那只荆棘鸟,在生命中不断寻找那株属于她的荆棘。在她将荆棘扎进胸膛时,她是知道的,是明明白白的,然而却依然要那么做。毕竟,最美好的东西总要用深创剧痛换取。她也换得了与拉尔夫短暂而美好的时光,以及从上帝那里偷来的戴恩……她用一生来承受这种爱而不得的无望的爱。
爱有千千万万种,有一种爱是需要用牺牲、用克制、用忍耐、用一生去承受的,这就是本书所体现的“荆棘鸟”式泣血之爱。
他们就像德罗海达那片土地一样,有干旱、有洪水,在干旱季节需要耐心等待雨季的到来,在雨季同样需要等待洪水的退去。爱也是一样有痛苦有欢乐,就如母亲菲奥娜用了一生才明白,原来她是多么地爱帕西,她用尽一生才明白这个道理;而梅吉也用一生来等待拉尔夫,才知道她是多么爱他,生命就在这悲欢中绵延不断……
二
许多人把这本书与《飘》相对比,称之为“澳大利亚的《飘》”,但是两者还是有很大的区别。《荆棘鸟》中的爱情观是传统意义上的,梅吉、菲奥娜都是隐忍、温柔和牺牲自我的女性;而《飘》中的斯嘉丽则是反叛自我,更强调女性的个人价值。前者是传统的审美,后者则带有女性主义的觉醒气质。不过二者的共同之处是,女性都是坚强而有韧性的。梅吉的坚强是接受命运的安排,温柔却有力量,执迷其中并伴随幽怨;斯嘉丽的坚强则更来得现代一点,果断和决绝甚至自私,并要把握自己的命运。
相对于传统意义上的“经典”概念,我倾向于把《荆棘鸟》和《飘》《朗读者》《海上钢琴师》《肖申克的救赎》等这些曾经的畅销小说或影视作品放在“亚经典”的范畴。相对于传统意义上的“经典小说”,如《德伯家的苔丝》《安娜·卡列尼娜》《罪与罚》《巴黎圣母院》等来说,“亚经典”小说在艺术上和对人性的描写上可能略逊一筹,格局上也没有那么大。但随着时间的推移,经过时间的筛选,有些“亚经典”会上升为“经典”也未可知。
对于这个问题,《肖申克的救赎》的作者斯蒂芬· 金就很不服气。他的许多小说都搬上过银幕。据说,按原著被改编为影视剧的比率,斯蒂芬·金可以排第二,第一则是莎士比亚。只要有机会,斯蒂芬·金就不惜大动干戈,跟人辩论到底:“通俗小说”绝非“垃圾”的代名词,受大众欢迎未必就不是好文学!
斯蒂芬自出道以来,其恐怖及玄幻小说大受欢迎。但他一直得不到主流文学界的承认,这也是他心里的一道坎。一怒之下,他写了一部主流小说,就是《肖申克的救赎》。而这部严肃的主流文学作品叫好又叫座。
2003年,他获得美国国家图书奖“终身成就奖”。消息一传出,美国文学界仿佛被捅穿了的马蜂窝,群情沸腾,不屑者有之,谩骂者有之,鼓掌叫好者有之。争论持续一个月,从报章杂志一直延续到颁奖会场。
“严肃文学”和“通俗文学”争论由来已久,它牵扯到文学典范的更替、文学史的流变等问题,“严肃文学”与“通俗文学”并没有一定的界限。我们现在承认的经典作家狄更斯就是从多产的通俗文学作家摇身一变成为文学史上浪漫主义的经典作家;而艾略特、乔伊斯等现代主义作家,将小说带入“晦涩难懂才叫文学”的窄胡同,也是文学史中争论的问题。
如果我们把文学放在一个更宽阔的角度,“只有好小说跟坏小说之分,没有严肃文学跟通俗文学之别”,文学也许就回归到文学本身了。
就《荆棘鸟》来说,类似这样的畅销书,并不妨碍它们可能从“亚经典”走向“经典”。这个问题只有等时间来回答。
《中国科学报》 (2021-08-26 第7版 书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