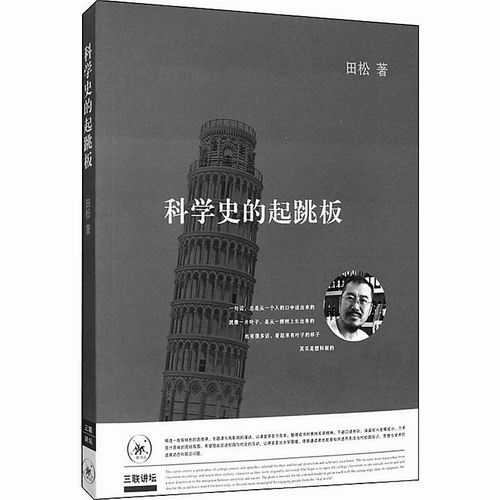
《科学史的起跳板》,田松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0年6月出版,定价:42元
■本报记者 李芸
“缺省配置”是南方科技大学人文科学中心教授田松常用的一个比喻,比喻我们头脑中固有的东西。这个比喻是同为科学文化人的北京大学教授刘华杰在2002年“发明”的。“缺省配置”原是计算机术语,指系统默认的配置,如预装的软件,窗口中设置好的颜色、字体、字号等。通常这些是可以调整的,只是大多数人终生都没有调整过。
《科学史的起跳板》根据田松在北京师范大学期间给博士生的科学史理论课上的讲课录音整理而成。这门课的主要目的是为博士生提供基础理论和专业训练,并引发反思。田松说:“描述‘缺省配置’是人文学术研究的基本功之一。”
《中国科学报》:书名“科学史的起跳板”中的“起跳板”是何寓意?
田松:跳远比赛的时候,有一个起跳板。选手要在这上面起跳才算数。起跳板的意思是说,对于科学史的从业者来说,这本书里讨论的是一些基础性的问题,算是专业起点。
听起来有点儿托大,其实是因为,这本书原本就是给我们科学哲学和科学史专业的博士生讲的科学史理论课。这是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刘孝廷主持的课程,我应邀讲了其中五讲。
《中国科学报》:本书虽名为《科学史的起跳板》,但科学史只是案例,全书6章中讲历史的有5章,分别是历史的本来面目、历史的细节、历史的再阐释、历史的功能和历史作为依据,你说本书的立意“不在于阐述具体的史实,而在于提供一种看待历史的视角”,具体来说是什么样的视角?这种看待历史的视角在史学界也是比较独特的吗?
田松:我的确只用科学史做了案例,主要讨论的还是历史观。书里没有对于某一段科学史作系统的阐述,而是把一些科学史片段作为案例,讨论历史是什么、怎样看待历史,以及怎样作历史研究、怎样写历史。
历史写作算是科学史专业的基础训练。将来学生作论文、做科学史就不用说了,哪怕是做科学哲学,也难免要对所要研究的对象进行描述、叙述、阐述、解释——这就是一个科学史的片段了。作为专业的研究者,如果对这些基本问题没有反思,依然沿用惯常的“缺省配置”的理解,那就太不专业了。
因为我只有五讲,不可能面面俱到,就选择了几个最为常见的、有针对性的,以及我比较有心得的几个问题,与同学一起讨论。
比如历史的本来面目,在惯常的理解里,当然是存在的,历史研究就是要发现这个本来面目。作为专业研究者,对这个观念就应该有所反思。再如历史的细节,我们习惯于宏大叙事,常常会忽略细节,不重视细节,所以我拿出来专门讨论。
如果要用一句话来回答“具体是什么视角”,我只能说,是一种反思性的视角。而反思,是一个研究者的基本素养。
你的第二个问题,我在本书的第6章《中国科学史的学术地图》里讨论过,中国科学史学界与历史学界长期处于一种相互隔绝的状态,我自己虽然努力读一些一般性的历史著作,但是对于史学界的普遍看法、一般观点,也不敢说了解。
我只能说,我讨论的这些问题,大多在史学界已经讨论过了,我以为应该是常识了。但在我与不多的历史系同学的接触中,感觉未必尽然。大家都是同样的“缺省配置”,有着共同的关于历史的初始理解,都是要经过反思才会有所转变的。这样想的话,我这本书对于一般历史系的同学也是具有参考价值的。
《中国科学报》:在第1章《历史的本来面目》有一个很有意思的话题:科学家写论文,通常不使用第一人称单数代词,而使用复数的“我们”;不少学术期刊要求用“笔者”作为第一人称代词。你认为原因何在?
由此你说到历史写作也是有人称的,“而只要是人写的,就会有人的立场、人的偏见和短见”。也就是说,历史永远没有真实的面目了?那会不会陷入虚无主义和怀疑主义?该如何看待“人写的历史”呢?
田松:其实,这些问题都能归结到同一对哲学问题:本体论的信念和认识论的立场。
本体论的信念是,是否相信存在一个外在的客观世界;认识论的立场是,人是否能够拥有全能视角(上帝视角),从而“不带个人偏见”地认识这个客观的世界。
我们的“缺省配置”对两者的回答都是肯定的。持有这种观念的人,会相信他“所描述的”就是“客观的”“本来的”,也就是说,他的描述与描述者无关,所以要淡化描述者的个人色彩,使用“我们”或“笔者”,回避“我”。
我对本体论信念问题采用现象学的“悬置”态度,不讨论。在认识论上,我反观自身,承认我是一个凡人,有我自己看不见的“缺陷”和“偏见”。
所以,如果历史存在一个本来面目,我不敢说,我所描写的就是那个本来的面目。由己推人,如果有一个人宣称他看到了本来面目,我肯定是不相信的。因为他跟我一样,也是一个凡人,也没有超能力。根据这个前提,我的结论自然是“只要是人写的,就会有人的立场、人的偏见和短见”。
当然,历史是存在程度不同的共识的。对于那些程度非常高的共识,比如“秦灭于公元前207年”,就可以说是一个确定的陈述。但这并不是绝对的,如果考古发现了新的史料,也可能会改写。这样的事情在历史上是经常发生的。
历史当然不是虚无的,如果是虚无的,历史就没有办法写了。但是怀疑,我不觉得是坏事。对以往的历史产生怀疑,才会产生对历史的新的解读。比如一百多年前的“疑古派”,就是把怀疑作为新史学的出发点。
人写的历史,也具有程度不同的稳定性,所以不用担心,历史不是虚无的,是相对稳定的。在稳定的公认的史料的基础上,会不断有新的史料,不同史学家对同样的史料会有不同的解释,这才有历史的丰富性。
《中国科学报》:在书中你说,“20世纪之前的历史学家可以写一部通篇不谈科学的历史著作,并且被视为优秀著作,到了20世纪,这已经不可能了。科学及其技术改变了我们生存的世界,以及我们看待世界的基本方式,甚至包括我们看待历史的基本方式”。科学技术让我们看待历史有什么改变?
田松:每个时代、每一个人,都会有关于世界是什么样子的基本想象,包括世界与我们的关系,世界是否有规律,世界是否变化、怎么变化……我们的生活是在此之上展开的。
我在书里也谈到了古人对这个世界的基本想象,里面充满着神灵。现代人对世界的基本想象是由数理科学建构起来的。
这个想象的核心是机械论、还原论、决定论的机械自然观:相信存在一个外在的物质的客观世界,这个世界如同机械一般,是物质的,没有内在生命(机械论);这个机械可以拆卸成一个个零件,零件可以替换,机械可以重新组装(还原论);科学能够精准地描述这个机械的运行(叫做科学规律),科学规律可以表述为方程,方程可以计算,人就可以根据方程的计算对这个世界作出精准的决定的预言(决定论)。我们对世界采取的行动,就是建立在这样一种基本想象之上的。
机械自然观同样渗入到我们的历史观当中。我们相信历史存在一个绝对客观的本来面目,如同我们相信存在一个绝对客观的外在世界。我们相信历史的演进存在某种必然的规律,如同我们相信外在世界的运行存在必然的规律。机械世界可以被还原成零件,历史也可以被还原成一个个史料。零件之间的关系是机械的,史料之间的关系也是机械的。比较我们的历史观和科学观,会发现二者有相当多的对称之处。
《中国科学报》:本书第6章在回顾了中国科学史数十年的发展后,讨论了未来方向,你提出要“走出科学史,走向文明史”,其背景和意义是什么?具体路径如何?
田松:前面说过,我观察到一个现象,中国的科学史学界与历史学界长期分立,井水不犯河水,而我觉得,这是需要改变的。科学史界对于科学史的理解已经发生了变化,不再认为科学史是科学,而认为科学史是历史。
然而,我又观察到一个现象,中国科学史学界的学者,普遍没有受过系统的史学训练。不仅以往如此,现在也是如此。各科学史机构在对各自研究生的学术训练中,并不包括系统的专业的史学训练。我觉得这是一个问题。
科学史学界有必要走出以往科学史相对封闭的范式,进入一般性的史学领域。我提出一个可行性的方案,就是与全球史接轨。在科学史与全球史之间,存在大量可以共通的地方。当然,我不能说“走出科学史,走向全球史”,那就失去了自我。所以我把“文明史”作为一个包括了“全球史”的更大的概念。
还有另一个背景,与我本人关注的问题有关。2007年我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访问时,接触到环境史,打开了一个新的世界。
从学科归属上,环境史被认为是全球史的分支。前面说过的对科学史的评价,也可以套用到环境史上:“21世纪之前的历史学家可以写一部通篇不谈环境的历史著作,并且被视为优秀著作,到了21世纪,这已经不可能了。”全球性的环境危机和生态危机是人类所必须面对的生存背景。历史学家当然也不能回避。
这样一来,我就觉得以往的科学史是不充分的。我就提出打通科学史与环境史,讲一个完整的故事。这可以作为走向文明史的具体路径。
2018年全国科学社会学年会上,我提出从STS(科学、技术和社会)走向STSE的学术纲领。E是环境或者生态。以往STS要么不谈环境,要么把环境作为社会的一部分,在面对环境问题时,解释乏力。
STSE有两种解释方案,一种是直接的,把E作为一个独立的因素,与科学、技术和社会相提并论,所以STSE学者必须面对环境和生态。另一种是深层的,把E作为背景,作为基础,人类一切活动都只能在E上展开。
STSE也是一个打通科学史与环境史的具体路径。比如化肥,科学史讲前半部分,从化学原理(S,科学)到化肥的可能性(T,技术),再到化肥产品的发明、化肥行业的出现,最后到粮食增产(S,社会),就结束了。这是以往STS的研究路径,也是通常科学史的叙事策略。
而按照第一种理解的STSE,则必须走向E,必须讨论化肥的环境影响和生态后果,这就从科学史走向了环境史。按照第二种理解的STSE,则需要从一开始就讨论E,每一个环节都讨论E。
从STS到STSE,我还有更具体的操作方案,就是从“科技产业链”到“科技产业污废链”。
最近看到一个消息,清华大学设置了科学史本科专业,没有设在理学之下,而是设在历史学之下,发历史学文凭。我觉得这个设置意味深长,对于科学史的范式转化,会有很多便利。
《中国科学报》 (2021-08-26 第6版 读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