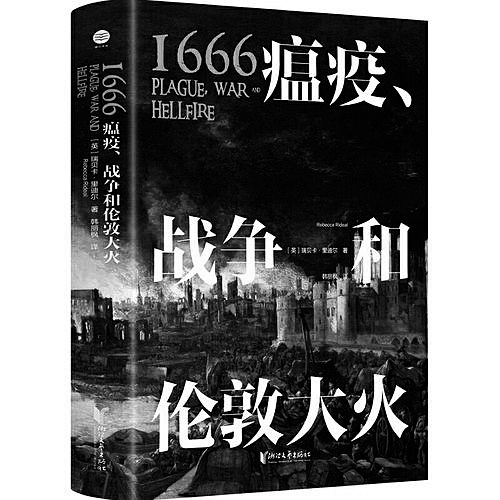
《1666:瘟疫、战争和伦敦大火》,[英]瑞贝卡·里迪尔著,韩丽枫译,浙江文艺出版社2021年6月出版,定价:88元
■杨靖
1666年伦敦大火过后,成立不久的英国皇家学会也面临困境:由于位于格雷沙姆学院的学会办公地点被伦敦市长劳伦斯爵士以灾后重建委员会的名义临时征用,学会成员无处可去。后屡经辗转,终于成功搬迁至诺福克公爵府邸所在的阿伦德尔庄园。当时谁也不曾料到,饱经忧患、颠沛流离的这一年,竟然会成为日后科技史家眼中皇家学会的“奇迹之年”。
根据英国纪实文学作家瑞贝卡·里迪尔在《1666:瘟疫、战争和伦敦大火》一书中的刻画,这一年堪称英国近代历史上的“多事之秋”:瘟疫、英荷海战以及伦敦火灾接踵而至,其中仅瘟疫一项便导致约十万人死亡(相当于伦敦总人口五分之一),令人触目惊心。然而,百年不遇的灾难并未摧垮英国人民的士气,相反却激发了人民众志成城重建家园的热情和决心——在这一过程中,英国皇家学会无疑发挥了引领作用。
在本书中,里迪尔以皇家学会会员塞缪尔·佩皮斯日记为线索,通过翔实的历史档案和名人书信,向人们展示改变历史进程的一系列重大事件,同时也揭示了英国建设现代化国家过程中的艰苦转型。
1665年至1666年间发生的大规模传染病(鼠疫)事件是继14世纪黑死病之后伦敦遭遇的又一次严重危机。面对这一严峻局面,皇家学会两位科学家首先从宏观角度对疫情报告和疫病预防制度提出了建议。
早在1662年,统计学家约翰·格朗特在《关于死亡率的自然观察和政治观察》一书中率先对世界范围内鼠疫暴发模式问题进行了探讨。在他的启发下,数学家威廉·佩蒂爵士开始绘制流行病地图,以此探究自然及社会环境与瘟疫暴发之间的关系。
疫情暴发后,佩蒂又赶赴一线深入调查,并与格朗特合作完成《死亡率表》(或称《生命表》)。通过研究分析,佩蒂推断,只有每周死亡人数超过100人时,伦敦疫情才真正开始。后来事态发展果如其言。
在统计调查过程中,佩蒂越发坚信:自然界存在确定不疑的且不以人意志为转移的“规律”。这一观念对同时代科学家影响很大:皇家学会天文学家哈雷受此启发,致力于观测行星的运动轨迹,并首次成功预测哈雷彗星的回归;17世纪末牛顿经典力学三大定律的发现,与此也不无关系。
佩蒂等人主要从事疫病防控的理论研究,时任皇家学会会长布龙克尔勋爵和学会秘书奥尔登堡则坚持奋战在抗疫前线,与皇家内科医师学会霍奇斯医生一道救死扶伤。霍奇斯率领医疗团队坚持工作(其中不少人因感染疫病不幸牺牲)。在六年后出版的《恶魔之症》里,霍奇斯阐述了“疫病的初发和恶化,以及疫病的症状和疗愈”,并详细描述了他亲眼所见的疾病的复杂性。这部医学著作与笛福小说《瘟疫年纪事》一同被视为伦敦瘟疫之年的历史记录,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除了上述“在籍”会员,学会一些“编外人士”也对疫情防控进行了积极探索,其中最著名的是纽卡斯尔公爵夫人玛格利特·卡文迪什。17世纪60年代,卡文迪什是除维多利亚女王外史上首位获邀参加皇家学会会议的女性,皇家学会直到1945年才接纳女性正式会员。
1666年,卡文迪什发表一篇“准科学”故事,名为《燃烧的世界》,后被视为英国乃至欧洲最早的科幻小说。作者借故事人物之口发问:瘟疫到底是对其他被感染身体体液的“模仿”,还是“像原子一样的小苍蝇身体”渗透所致?非常明显,借助古希腊哲学传统的“原子”这一概念,卡文迪什意在通过运动中的“实体”构建现代病理学。这一思路,显然远远超乎她的同时代人。
即便在瘟疫肆虐期间,学会各项工作也在有条不紊地向前推进。学会会刊《哲学学报》第七、八两期由于伦敦印刷商出逃,被迫改在牛津出版,由当时身在牛津的佩蒂和科学家胡克等人负责此事。他们一方面坚持伦敦未竟的科学实验,一方面加紧审稿排版,临危不乱,展示出皇家学会高超的学术素养和良好的道德风范。
会长布龙克尔勋爵时常需要陪同国王和约克公爵(即位后称詹姆斯二世)外出视察;秘书奥尔登堡负责整理学会资料,并与欧洲大陆科学家(如斯宾诺莎、莱布尼茨等)保持学术沟通和交流;佩蒂等人则忙于舰船及武器装备改进工作。
皇家学会资深会员伊夫林是伦敦大火后第一时间(一周内)向政府递交重建方案的三位专家之一,另两位分别是雷恩爵士和胡克。
由街头面包店着火引发的全城火灾损失惨重:四天内,大约有7万人流离失所,13000座房屋、87座教堂和52座行业会馆被烧毁。路德盖特、纽盖特和奥尔德斯城门遭到严重破坏。市政厅成为废墟,海关大楼不复存在,圣保罗大教堂被烧毁,贝纳德城堡支离破碎,皇家交易所也被夷为平地,累计损失约为1000万英镑。跟随国王出巡的权臣克拉伦登伯爵哀叹,伦敦“这座城市最富裕的部分”已化为灰烬。
国王在视察灾情后发出呼吁,希望自己能在有生之年看到一座比“被大火吞噬的”伦敦“更美的、设施齐全且能防范火灾”的城市,并责成皇家学会和伦敦市政府通力合作,尽早拿出具体方案。
伦敦火灾重建委员会名单上共有六人,其中三人由国王任命,以雷恩为首;另外三人由伦敦市长指派,以胡克为首,共同负责总体拆迁和重建工作。伊夫林、雷恩和胡克提出的三个重建方案在实践中相互取长补短、融会贯通,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胡克和雷恩两位建筑设计师在此过程中也爆发出惊人的能量:高峰时期,胡克每个月完成90户居民地基勘测(同步负责学会实验工作),并设计和兴建了包括圣马丁教堂在内的若干公共建筑。雷恩很早就将他的数学技能和建筑设计知识运用到实际操作中,他负责设计伦敦的50余座公共教堂,一律采用巴洛克风格,选用白色石料,线条简洁,细节处充满生机,赢得广泛赞誉。
除此之外,胡克与雷恩还奉命共同设计建造伦敦大火纪念碑,计划在镂空的碑顶安装巨型天文望远镜——尽管这一构想未能实现,但这座纪念碑日后的确成为伦敦的新地标。
重建方案在实践过程中虽然日臻完善,但由于牵涉到王室和伦敦市政府以及普通市民三方的切身利益,实际操作层面遭遇了不少困难,因此亟须通过立法加以解决。
在皇家学会倡导和王室支持下,英国历史上首个“重建法案”于伦敦火灾次年获得通过。于是,伦敦城主体改建工作得以顺利实施——内城街道被拓宽,伦敦最大的地下河弗利特河被疏浚,并沿河岸开挖出40英尺宽的间隔,有火灾隐患的行业被迁移出高风险地区,市中心大部分街道的格局则保持不变。同时,法律严格规定,新建筑必须由砖石建成。由此,伦敦的城市美学“被永久改变”。
1666年,避居林肯郡乡间伍尔索普庄园的牛顿相继发明微积分和反射式望远镜,同时发现日光七色光谱和万有引力定律,从而一举奠定经典物理学的理论基础,科学史家将这一年称为牛顿的“奇迹之年”。事实上,这也是英国皇家学会的“奇迹之年”。正如里迪尔在本书结尾引用大诗人德莱顿《1666:奇迹之年》一诗所说,由于政府与民间以及科学家的共同努力,历经劫难的伦敦,宛如“灰烬中浴火重生的凤凰”,必将成为人类历史上“历久而弥新的奇迹”。
《中国科学报》 (2021-07-22 第7版 书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