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工智能的崛起正在重塑人类文明的认知图景。从ChatGPT的惊艳亮相到各类大模型的竞相涌现,我们目睹了一场静默却深刻的认知革命。在这场由AI领衔的变革中,一个永恒的疑问愈发清晰:当机器也能吟诗作画、运筹帷幄时,人类灵魂中那不可复制的灵光,将栖居何处?
这不仅是技术伦理的命题,更是关乎人类自我理解的哲学叩问。
2024年3月,由亚当·弗兰克等三位科学及哲学领域的顶尖学者合作完成的先锋之作《盲点:科学为何不能忽视人类经验》正式发行。不到一年,该书的中文译著《何为科学》即被推出,引发各界学者关注。
三位作者在此书中创造性地提出了一个常被人们忽视的概念:科学的“盲点”。
“盲点”一词的生理释义是视网膜上没有感光细胞的区域,即无法产生视觉的角落,后来被进一步引申为认知上的空白和偏误。亚当·弗兰克等指出,现代科学中最大的“盲点”在于,我们遗忘了人类的直接经验才是科学知识的本质来源与坚实支撑。
近日,在河南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何为科学》的主要译者、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周程与河南大学人文社科高等研究院院长、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张宝明以“AI时代的科学盲点”为主题,围绕《何为科学》一书进行了对谈。
两位学者分别从哲学、历史学及语义学等学科视域对科学的“盲点”进行了解读,重新审思了几个“盲点”之下的隐蔽议题:现代科学的“盲点”究竟由何而来?该如何消解?AI重构认知范式的今天,我们又将如何超越“盲点”,保全人类作为意义承担者与行动主体的尊严?
对谈人简介:
?
周程,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科学技术哲学教研室主任,北京大学科协常委,中国科协-北京大学科学文化研究院副院长。
?
张宝明,河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河南大学人文社科高等研究院院长。“新世纪百千万人才工程”国家级人选、全国文化名家暨“四个一批”人才、国家“万人计划”哲学社会科学领军人才。
1 人人患有“经验失忆症”
张宝明:
在人工智能成为热议话题的当下,周程老师主导翻译的《何为科学》一书的出版显得尤为适时。该书以科学为主题,但更多的还是探讨了科技带来经验“盲点”问题。
我曾在一次关于“AI时代人文学”的讲座中无意间提出一个观点:尽管人类科技不断进步,并在这一过程中诞生了许多巨著,但在人工智能浪潮来临之际,我们更需要思想的巨人。
这本书的问世,似乎正是为了回应这一需求。三位作者在书中首次指出,现代科学(更多的是科技)的一个基本盲点在于,我们遗忘了人类的直接经验乃是科学知识的本质来源与坚实支撑这一基本事实,进而将科学实验和实证研究还原为验证理性的唯一路径。
就像本书提到的“工作间”,科学家的实验都在工作间完成,直接经验在这个过程中被悄然遮蔽了。待人类经验彻底淡出视野的时候,我们慢慢就会产生一种“经验失忆症”。
周程:
您提到的“经验失忆症”是此书中非常重要的一个概念。《何为科学》这本书主要就是讨论这一问题,也就是科学为什么不能够忽视人类经验?
我想举几个日常生活中的例子。比如导航系统,原本是辅助工具,但如果长期依赖它,可能导致驾驶者对自身导航经验的逐渐遗忘。再比如温度感知,人们往往依据天气预报的数据来判断外界温度,而非依赖于自身对温度的直观感受。
这些现象表明,一种替代经验的文化正在形成,其中科学数据的地位日益提升,而个人的直接经验和感受则被边缘化。
我们不自觉地将一种抽象的、数学化的世界观植入科学体系之中,仿佛科学提供了一种“上帝视角”,能够赋予我们关于物理世界本质真相的描述。三位作者认为,这些盲点势必会影响科学自身和社会的发展,有的甚至会产生不良影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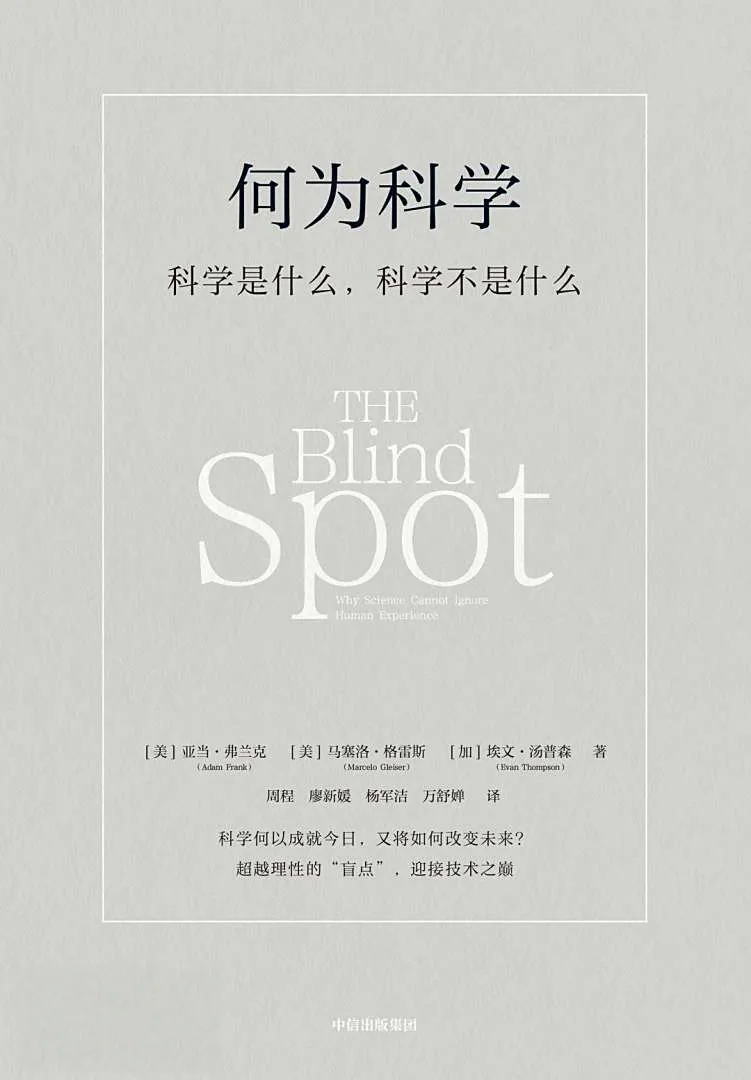 《何为科学》(2025年4月中信出版社出版)
《何为科学》(2025年4月中信出版社出版)
2 科学与人文的理念原本“同根”
张宝明:
正如您所说,现在幸福感的体验已深受形而上学的世界观影响,它以科学的名义对个体进行渗透、束缚甚至绑架。因此,三位科学家强调重建科学理念的整全性是必要的。
审思科学的“盲点”,还牵涉到一个科学和技术的关系。彼得·伯克在《什么是知识史》中告诉我们,作为从“信息”提取的“知识”,需要从前学科或说非学科的背景去理解。从传统技术到现代科学的转型中,人类经验的角色经历了从核心驱动力到系统性遮蔽的深层演变。
在古希腊时期,科学被称为自然哲学,科学与人文浑然一体、同源共生,是有价值导向的。而现代科学并不如此,它试图从自然的理性秩序中体察合理的社会规范,寻找一种好的生活标准。这种把理性解读为合理的做法是我们所陌生的。
科技的“盲点”在于它对人类经验的殖民化,更确切地说是,对人类经验的吞噬。因此,我们要警惕还原主义、客观主义、物理主义等方法论压倒主观质素的倾向。
周程:
作者在这本书里面多次谈到:科学的原始发展来源于身体对于周围世界的一种感受。从17世纪起,随着显微镜、望远镜等科学仪器的发明与应用,人类对经验世界的感知逐渐转移到了实验室环境中,通过观察和测量,将所见现象转化为概念,再通过数据化手段进行建模。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开始将这些模型视为真实和客观的存在,而忽视了我们对物质世界的直观感受。这就使我们对科学产生了一些认知偏差,即所谓的“盲点”。
科学的演进自其发端便根植于一系列信念之中,正如我们在大学里所学习的——世界是物质的,物质是运动,运动是有规律的,规律是可以认识的。基于此,科学得以建立。实际上,在开展科学研究之前,便已存在这样一种信念作为支撑,而这些信念从未得到过确凿的证明,同样无法证明其绝对的非真实性。
张宝明:
今天我们置身于一个知识膨胀的时代,就像货币贬值一样,现在知识的获取极其容易,通过AI很快就会获得。学富五车、才高八斗的老教授们不说黯然失色,最起码少了一份神秘感。信息也在爆炸,同时更加深了经验的萎缩。在人工智能时代,该如何面对人类经验的萎缩,是我们迫切需要思考的问题。
周程:
是的,人工智能的发展让我们看到其在许多领域超越了传统教授的知识水平。但同时也存在一些问题。如果不谨慎,利用人工智能扩展知识视野也可能带来一些副作用。比如大语言模型就暴露了人工智能技术在发展过程中存在深层的认知盲点。
尽管有学者指出,这些模型在某些语言生成任务中展现出高度的专业性,似乎可以被赋予某种“知识能力”。然而,这种对其知识性的强调掩盖了一个关键问题:模型的输出建立在对大规模语料中统计模式的学习之上。它们生成的文本仅仅是对语言结构的模拟,而非对现实世界的理解。模型在某些方面看似超越人类,但本质上仍有差异。
张宝明:
人工智能缺乏历史感,它既无理解也无意义,产出的内容千篇一律。当AI将“乡愁”解构为经纬度坐标时,它剥离了游子望月思乡时的身心经验,这正是科学主义简化生活世界的典型症候,也是河南大学人文语义学交叉学科所研究的学术命题。
语言是人类认知生活并进行表述的方式和过程,每一次表述都是具体时空语境下的人类语言交往实践,每一种语言都包裹着一个特定民族与众不同的经验和意义。人文语义学就是要剖析语词以及生活经验文化观念的语义学问题,揭示观念词背后深层的社会经验,并由此成为一种“经验的社会史”。
在这个意义上,《何为科学》为人文语义学下一步的转型和提位赋予了很重要的意义资源、话语资源和理论资源。
张宝明:
科学的“盲点”喻示着一场意义危机,这也是文艺复兴尤其是启蒙运动以来的人文主义学者赓续不断的话题。关于科学怎么样充实人类经验的权重思考,中西方都发生过。如1922年爱因斯坦和柏格森围绕时间的“绵延性”的争论和1923年丁文江和张君劢关于科学与人生观的论争。
在人工智能时代,我们一方面要求科技越来越精细,手表走得越准越好。但在《何为科学》的作者看来,时间越准、盲点越大,与人的直接经验越来越远。人工智能越发展,就越摆脱哲学的承诺和人文的关怀,这是目前人文学者最关心的问题。
人的问题是终极问题。雅思贝尔斯说,人永远是目标,其他都是手段。
周程:
现在的关键问题是如何解决“盲点”,《何为科学》的作者没有谈到,其实就是用人文社会科学去修复,解决在科学界出现的一些问题。
在这一背景下,“以人为本”的人工智能倡议并不是一种伦理补丁,而是一种对科学主义盲点的根本超越。它重新确立了人的价值、解释能力与实践经验在人工智能建构中的核心地位,提醒我们,任何技术系统的意义与正当性,最终都必须回到人的经验世界与生活语境中去理解与评价。
唯有如此,我们才能真正摆脱那种将科学误认为全知的神话,在被技术深刻重塑的时代,重建人类作为意义承担者与行动主体的尊严。
张宝明:
在我看来,科技发展的终极伦理,应是守护那些无法被算法穷尽的“生活世界”之质感,正如庄子“浑沌之喻”守护不可解析的生命整体性一样——因为所有科学的结构不变量,终将在人类经验的土壤中重生。“盲点”的扩大不是科学本身造成的,而是由于科技的使用不当或是误解造成的。
周程:
这中间还有一个问题,就是科学哲学里面经常谈到的反身性。当我们强调人类经验的重要性时,是不是也有反身性,也会形成盲点?
我们强调经验的重要性,但同时也要认识到经验本身可能存在的不真实性。随着深度伪造技术的不断进步,其逼真度越来越高,我们在与这些技术互动的过程中形成的经验,同样需要审慎对待。
特别声明:本文转载仅仅是出于传播信息的需要,并不意味着代表本网站观点或证实其内容的真实性;如其他媒体、网站或个人从本网站转载使用,须保留本网站注明的“来源”,并自负版权等法律责任;作者如果不希望被转载或者联系转载稿费等事宜,请与我们接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