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是生命体最重要的外部环境因素,也是人们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照明介质和工具。对科学家而言,光更深层次的意义还在于对人类生命健康的深刻影响。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以下简称“中国科大”)教授薛天研究团队在国际上开拓和推动了“光感受调控生命过程”的研究,取得了多项原创性成果。近5年来,4篇成果发表在《细胞》杂志上,多次荣获“中国科学十大进展”“中国生命科学十大进展”等奖项。
日前,薛天团队荣获2024中国科学院杰出科技成就奖——基础研究奖。薛天个人荣获2024年中国科学院年度创新人物称号。
“这是对我们团队脚踏实地做基础研究工作的认可,我感到非常荣幸。”薛天表示,只有在科学知识的引领下,合理、智慧地使用和利用光资源,才能让光真正成为人们健康生活的伴侣。
 薛天(一中)研究团队部分成员合影。实验室供图
薛天(一中)研究团队部分成员合影。实验室供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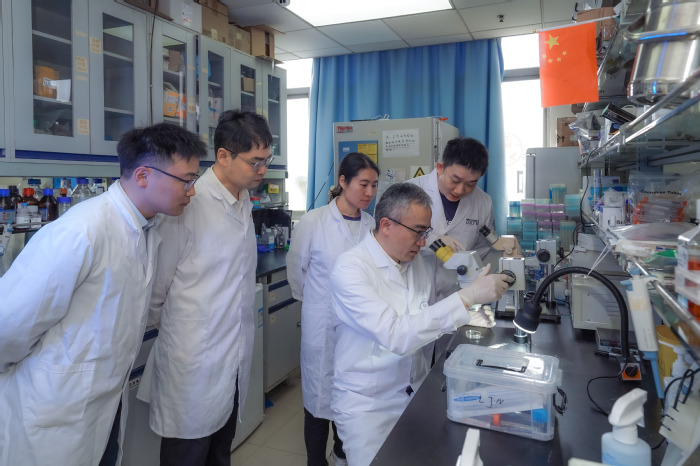 薛天与团队成员在做实验。实验室供图
薛天与团队成员在做实验。实验室供图
?
开拓光感受调控生命研究新领域
光是生命之源。生命体从十几亿年前诞生到整个进化过程,全都是在太阳辐照下进行的。在进化的单细胞阶段,生命体已经开始演化出了对光的感受能力。“比如,水藻随着太阳光上浮或下沉,选择最有利于它的生活环境。”薛天说,这其实就是光感受调控生命最简单的形式。
感受外部环境是生命体最根本的基础功能之一,人类80%以上的信息是靠光感受输入,光感受调控生命是十分重要的关乎生命本源的问题。
随着社会的飞速发展与现代化进程的加速,人造光源的出现改变了自然光照环境。大量的公共卫生学调查显示,夜间光污染与肥胖、糖尿病等代谢性疾病的发病率上升密切相关,但缺乏因果性证据。
“从生命的进化、生命体的基本特征以及人类生命健康这三个角度来看,光感受如何调控生命都是很值得回答的重要科学问题。”薛天说,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绝大多数视觉领域的研究者都在关注光感受中的图像视觉问题,鲜有人深入研究光感受调控生命过程的机理。
薛天最早研究这一问题缘起于他在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医学院求学和工作的经历。他所在的实验室发现了第三类感光细胞——自感光视网膜神经节细胞,简称ipRGC,改写了百余年来教科书上视网膜内只有视锥、视杆两类感光细胞的认识。
这个全新感光细胞的发现,引起了薛天的浓厚兴趣。2011年,他独立解析出了ipRGC的光信号转导分子机制,研究成果发表于《自然》。
“随着ipRGC的发现以及感光分子机制的明确,很自然地我们就会想知道这样一个古老的感光细胞,在生命体中执行什么样的生理功能。”也是在这年,薛天回到中国科大建立了“光与生命”实验室,开始着手回答这个问题。
10多年来,薛天带领团队首次阐述了光影响大脑发育、调控血糖代谢和诱发抑郁样情绪等的神经环路机制,揭示了前端视网膜的发育与衰老过程中的关键基因,首次实现哺乳动物裸眼近红外图像视觉能力,开发了用于黄斑变性治疗的药物已获批一类新药的临床试验,系列工作推动了光感受神经生物学的基础科学知识和转化应用前景。
穷尽一切手段趋近于真相
无论是人或是其他哺乳动物,眼睛只能感受到380至760纳米的可见光。能否突破自然界赋予视觉感知的物理极限?马玉乾作为薛天回国后带的第一个博士研究生,尝试利用一种可吸收红外光发出可见光的上转换纳米材料,导入小鼠视网膜中,首次实现了小鼠裸眼近红外图像视觉能力。
成果在2019年经《细胞》发表后,得到广泛关注。《科学》评论“如果同样技术在人类身上奏效,会为士兵提供夜视能力,无需佩戴夜视仪,并有可能对色盲等疾病产生治疗效果。”该研究获2019年“中国生命科学十大进展”。
“薛老师教导我们,做科研要把短中期目标和长期目标有机结合,短中期目标的不断达成,既积累了经验、培养了信心,也证实了实验室的持续创新能力,同时要保持初心,围绕原创性重大科学问题长期持续攻关。两者的结合才会产生脚踏实地又仰望星空的感觉。”已担任中国科大特任教授的马玉乾说,自己刚进实验室时做的一项基础研究课题,持续了13年,最近刚完成了机理解析,正开始总结成文。
史逸铭是第二个进入薛天实验室的博士研究生。他与合作者以小鼠为模型,从分子到细胞层面上解析了光如何影响大脑神经元突触的早期发育。
史逸铭清晰记得,这项研究源于薛天参加了一场学术会议,其中一个学术报告谈及光影响早期脑发育,这和实验室此前观察到的ipRGC感光细胞在发育早期就开始感光密切相关。受此启发薛天走出会场,立即拨通了启动该研究项目的电话。
“研究刚开始时进展很顺利,但在后期实验中‘卡壳’了,光对脑突触发育的调节作用,究竟会对小鼠成年后产生怎样的生理行为影响?”史逸铭一段时间内都没有思路。
在一次偶然的数据分析中,史逸铭在其另一个项目的行为实验里发现了一个特殊现象:ipRGC感光蛋白被敲除的成年小鼠,其学习速度显著慢于正常小鼠。很快,他提出,小鼠幼年时期接受的环境光通过增强大脑皮层和海马的突触发育,强化了动物成年后的联想学习能力——而这一能力也恰恰正是皮层和海马的关键特征之一。这一想法也在随后的实验中被证实。该研究成果发表于《细胞》,获2022年“中国神经科学重大进展”。
史逸铭说,“做研究经常遇到各种问题,真正好的学者会将各种科学问题时时放在心头,同时善于在不同的科研工作中寻找可以偶联的线索。这正是薛天老师的那通电话带给我的宝贵思维。”
孟建军从复旦大学毕业后,进入薛天实验室进行博士后阶段研究。他同样也是经过多年攻关,发现经过短波长蓝光的照射刺激后,小鼠和人的血糖代谢能力都会显著降低。这为长久以来就发现的夜间光污染导致糖尿病、肥胖等代谢性疾病高发的现象,提供了神经生理学解释。该成果发表于《细胞》,获2023年“中国科学十大进展”。
“我们实验室的课题往往周期很长,体量和内容都很大。因为我认为实验科学是在当下的条件下,穷尽一切技术手段和办法趋近于真相的艺术,下苦功夫不抄近路,是一个真正的科学家最应该遵守的原则。”薛天说,逼近真理的科研过程,无论要历经多少时间、投入多少精力,都是必须且值得的。
仍有重大科学问题待解决
对于未来,薛天认为“光与生命”这个主题仍有重大科学问题有待解决。例如,光感受里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科学问题是,人视网膜中的黄斑和中央凹的形成机制。
“在哺乳类动物中,只有高等灵长类才具备黄斑和中央凹。而且它在眼睛中占比约1%,大约1平方毫米,却是人类形成精细视觉的关键。”薛天表示,黄斑和中央凹的发育形成机制是视觉领域的极为重要的“圣杯”问题,值得长期深入研究。
“而在‘眼-脑’连接调控生命过程方面,我们近期比较关注光与节律的关系,以及昼夜行动物行为的来源。为什么有的动物在夜间活动,例如小鼠;有的动物在白昼活动,例如人类。”薛天说,人们对这一系列科学问题背后的神经生理学机制知之甚少。
随着对光与生命健康关系研究的深入,薛天提示人们要特别关注人造光的光谱、光强以及光照时间。
具体来说,人们在白天应该接受充足的太阳光照射,办公室内可布置短波长的冷光源;夜晚时,不宜过多暴露在短波长的蓝光之下,客厅、卧室优先选用暖光源。
在转化应用领域,薛天团队已研发出了一种多色光源,可实现对人的视网膜中每一种感光细胞相对独立调控。这样既能在夜间保证视觉体验的同时,又不产生过多光污染问题,进而减少光污染对于情绪、节律、睡眠以及代谢等的影响。
“一个科学工作者的学术生涯是很短暂的,有机会能走在世界前沿,尝试解决重大科学问题是十分幸运的。”薛天表示,“同时科研工作又是一个持续积累的过程,需要科研人员静下心来,不能急功近利,一步一步按照科学逻辑抽丝剥茧,一个个问题去解决,才能在科学研究中不断进取,有所作为。”
薛天透露,实验室又有一项工作近期已被《细胞》接收,即将发表。“我们通过上转换材料隐形眼镜的方式,实现了人类红外视觉能力。”
版权声明:凡本网注明“来源:中国科学报、科学网、科学新闻杂志”的所有作品,网站转载,请在正文上方注明来源和作者,且不得对内容作实质性改动;微信公众号、头条号等新媒体平台,转载请联系授权。邮箱:shouquan@stimes.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