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春节,新冠疫情的持续催生了一个新词“原年人”——原地过年的人。如果没有疫情,这些“原年人”或许会像往年一样,在节前踏上不同方向的列车,加入春运的洪流,再于此时由家乡返回城市,从乡村青年翠花、小娟、二柱子再度变回都市白领露西、托尼和乔安娜。
1947年,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中分析了中国基层社会的结构。农民的半截身子像植物一样扎根在土里,由此构成了“生于斯长于斯”的熟人社会。而在70多年后的今天,人口流动已成为时代的关键词之一。
大规模的人口流动等因素给今日的中国乡土社会带来了怎样的变化?而身处这变化当中的我们,又有着怎样的切身感受呢?
回乡过年的亲切感与不习惯
“虽然也能在网上发视频、发红包,但相比于往年十几口的大团圆,今年一家三口的年还是过得有点冷清。”这是陈娟这个“原年人”今年过节的感受。
因为疫情,陈娟和丈夫带着五个月大的孩子,留在工作地、广东一个城市里过年。看着年幼的孩子,陈娟脑子里浮现的全是自己小时候过年的场景。
“80后”陈娟出生于山西中部一个村庄。记忆里,从腊月二十几起,家家户户就开始张罗过年的食物,其中最重要的一项就是蒸花馍。家里的大大小小聚在一起,商量着面怎么捏、枣怎么贴,巧手的主妇们会捏出特别漂亮的花样,然后用超大的蒸笼上锅蒸熟。
“不过这两年,我们家已经不蒸了,觉得太累,不如买现成的。”陈娟说,“这些年来,村里过年的习俗越来越简单了,有的改良了,有的消失了。”
以前,在陈娟村里,过年前一天,家家户户都会在自家院子里垒旺火——把炭垒成一堆,贴上写着吉利话的红纸。初一一早起来,第一件事就是把旺火点着。邻居们也会一起垒一个大大的旺火,到了正月十五这一天,各家各户就拿着花馍去烤。“现在,各家院子里的旺火改成了蜂窝煤,而用大旺火烤花馍的仪式已经消失了,各家自己用电饼铛烤一下,意思一下就算了。”陈娟说。
过年物事简化带来的直接后果,是无事可做。“这说不上好还是不好,因为这确实减轻了人们的家务负担,但同时,大家聚在一起做事的热闹劲儿没有了。这几年回家过年,就是一人一个手机,打游戏、看抖音、抢红包。”
村里的年轻男人基本都出去打工了,孩子跟着妈妈和爷爷奶奶生活。陈娟上大学时放假回家,还能跟儿时的朋友聚聚,毕业工作后回家,几天的假期只够陪陪家人。这两年更是没得聚,因为回家过年的小伙伴越来越少了——有些把父母接到城里过年,有些干脆就不回家了。
因为自小学习成绩好,陈娟在村里小有名气。每年回家,“走在路上,人人都认识你,人人都和你打招呼”,经常被拉住聊上半天,被乡邻各种夸赞。
陈娟很享受熟人社会中的这种亲切感,同时也有些不习惯。“因为夸你的前提是先要打听你。”陈娟说,“打听的内容事无巨细,比如多大了?生孩子没有?还没生?赶紧生啊,年纪大了生孩子可不好!不是有什么毛病吧?又比如做什么工作?在哪儿工作?一个月赚多少钱?”
陈娟有段时间没找工作,过年回家碰上村里人就照实说。第二天,家里人告诉陈娟:“我出去碰上谁谁了,说你家陈娟没工作啊,那怎么生活?”还有一次,陈娟被一个阿姨拉着手聊了半天,让她“赶紧生孩子,有毛病赶紧去看”。尴尬的是,陈娟怎么也想不起来,对面这位阿姨是谁。
即便如此,回家过年依然是陈娟最大的期望。 “不管大家聚在一起干什么,只要能见到家人,哪怕只在吃饭的一两个小时里,十来口人团坐在一起,吃着聊着,就实现了过年最大的意义——团聚。在家里待几天,能给我充满一整年的电。”
“年味儿越来越变了”
如果说陈娟的所见所思是基于普通人的个体感受,那么武汉大学社会学院研究员杨华对乡土社会变化的观察,则是在个人感受外,还多了一重专业学者的视角。
从2007年起,杨华每年至少会花三个月时间在全国各地的农村作驻村调研。今年1月,他出版了《陌生的熟人:理解21世纪乡土中国》一书,即是由他这些年在驻村调查过程中写作的随笔结集而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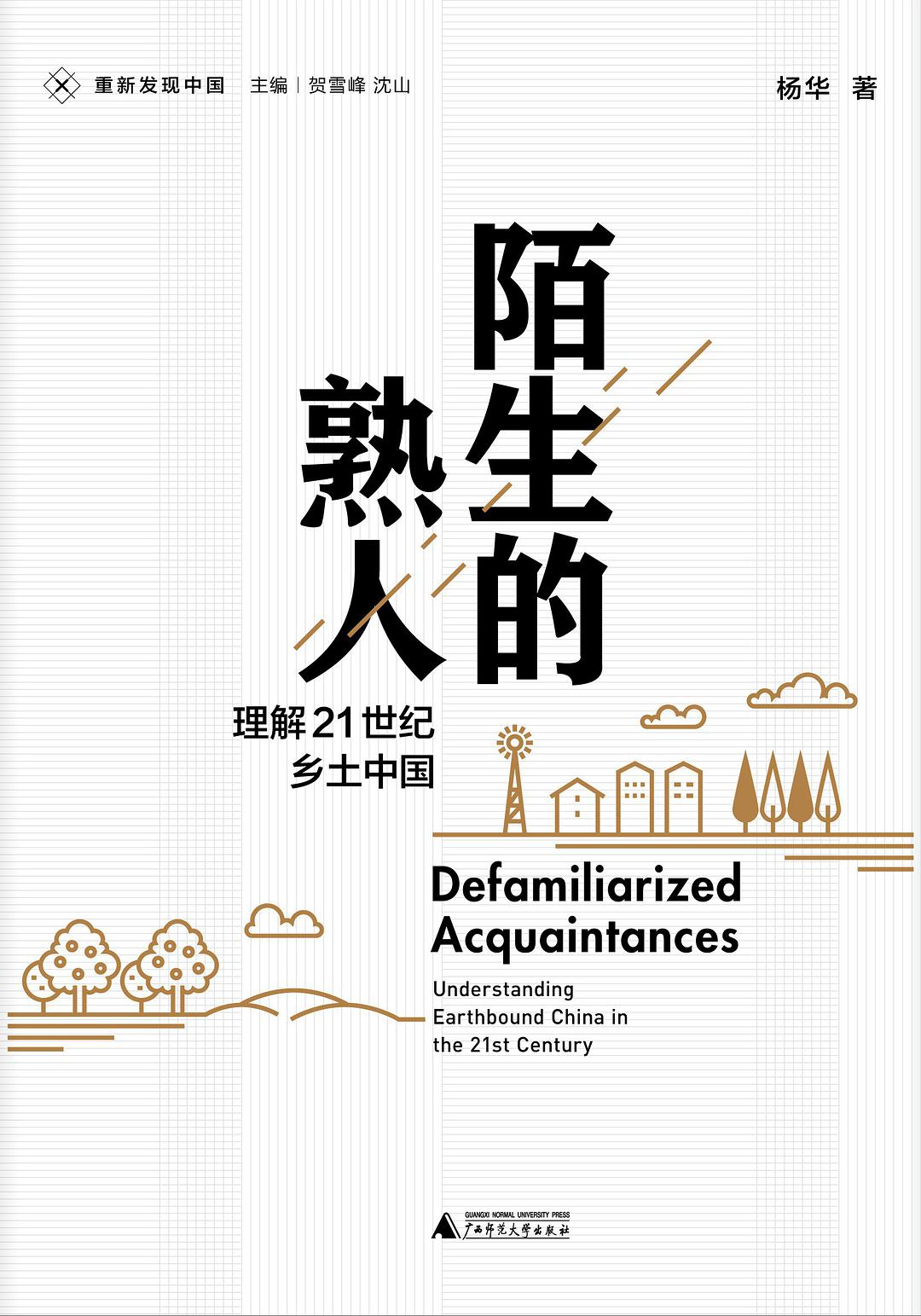
《陌生的熟人:理解21世纪乡土中国》,杨华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1年1月出版,定价:47元
每年春节,杨华也会观察自己家乡——湘南农村和其他农村地区熟人社会的变化,比如人情。“熟人社会不仅仅是指人们之间的熟悉,同时也囊括了人际交往、人情世故、互帮互助以及社会规范等一整套的运行制度。”杨华说。
在杨华看来,与春节本身的仪式感不断弱化相关联的因素之一,是其要让位于人们之间相互建构关系、保持熟人感情的功能。“在乡村传统社会中,节气礼俗等一整套制度是伴随着农民的生活秩序和生命周期展开的,比如婚丧嫁娶、逢年过节。但随着市场经济的繁荣和打工潮流的兴起,农民一年中大部分时间是脱离村庄的,所以每年春节返乡就成为农民摆酒办事走人情的重要窗口。”
而如今春节期间农村的人情是比较重的。杨华在调研时看到,有些地方春节期间的人情支出高达农民家庭一年三分之一的收入。“然而,正是因为人情仍旧是村庄熟人社会最重要的维系机制,仍然带有仪式性和交往性的功能,所以没有人能够摆脱人情的压力。青壮年带着一年的积蓄返乡,也抬高了农村人情的标准。所以,春节期间我们既能看到人情酒席的热闹,同时也能听到农民感叹压力很大。”
“城里人可能觉得年味儿越来越淡了,在农村则可能会觉得年味儿越来越变了。回家过年似乎越来越成为返乡农民的一种负担,包括人情的负担、竞争的压力,等等。过年回家好像不再那么轻松愉快,而变成某种任务了。”杨华说。
而对于那些已经成年并进入社会的“80后”“90后”农民来说,虽然大家都生于同一村庄、一起成长,但在外出务工、经商之后,不仅空间分化、职业分化、社会分化大,而且经验分化、价值观分化、社会关系分化等也都很大,又缺乏日常化的交流、沟通。“因此,即便是熟人关系、老表关系、堂兄弟关系、邻里关系,但相互之间已不再熟悉,成为典型的‘陌生的熟人’。”杨华说。
理解21世纪乡土中国
每年春节期间,随着青壮年返乡,农村的熟人社会会暂时性地重新变得完整和有活力。但对于杨华等学者来说,他们关注更多的则是那些平常的日子里,中国乡土社会所发生的改变。
在《乡土中国》中,费孝通将中国农村称为“熟人社会”。在这个熟人社会里,大家都沾亲带故或者非亲即故,社会结构呈现一种“差序格局”,人们行事注重亲情和礼俗规约,但讲究亲疏远近有别。
2003年,武汉大学社会学院教授贺雪峰出版了《新乡土中国》,在书中呈现出20世纪90年代至21世纪初中国农村社会的变化。在这一时期,受市场经济和人口流动等因素的影响,农民对村庄的归属感正在减弱,不仅“身体不在村”,而且“人心不在村”了。村庄社会的关联日渐松散,人际关系日益理性化,村庄公共性日趋消弭。此时,村庄已经不再是农民知根知底、互帮互助的“熟人社会”,而是转变为“半熟人社会”。人们的行为越来越少地遵循乡土逻辑,而越来越多地拥抱市场逻辑。
进入21世纪,农村人口流动进一步加剧,市场经济渗透进一步加深,城镇化步伐进一步加快,在此影响下,中国乡土社会又产生了哪些新的变化?杨华在《陌生的熟人:理解21世纪乡土中国》一书中作出了一些解答,展现出了自己对当前农村的纠纷调解、人情往来、村庄选举、代际关系、婚姻爱情等主题的观察和思考。
在杨华看来,中国乡村社会的变化可以归结为三个方面,即村庄治理之变、社会结构之变与农民价值之变。“这三个层面的变化在短短一二十年里集中发生,它们之间的内部关系非常复杂且相互影响。应该说,市场经济的发展和村庄治理逻辑的变化是主导因素,二者共同推动了农民生产生活和社会交往的转变。”
在杨华看来,现代化、工业化和城镇化是中国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农村的衰败是无法阻挡的。在这个过程中,城市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增长极,农村则是稳定器和蓄水池。乡村振兴不是要把农村建设得像城市一样繁华、现代化,而是要让留在农村的农民能够享受基本的公共服务,让进城失败的农民还能够回得去、住得下,还是进城农民能够向往的故乡。
“所以,乡村振兴的重点应该是文化建设和村庄基本公共建设。只要农村还是村庄,熟人社会就还存在,只是可能以不同的方式存在。比如县域扩大的熟人社会,再如‘陌生的熟人’,即虽然是熟人,但彼此之间不再熟悉熟识,这也是熟人社会的一种存在类型。”杨华说。
版权声明:凡本网注明“来源:中国科学报、科学网、科学新闻杂志”的所有作品,网站转载,请在正文上方注明来源和作者,且不得对内容作实质性改动;微信公众号、头条号等新媒体平台,转载请联系授权。邮箱:shouquan@stimes.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