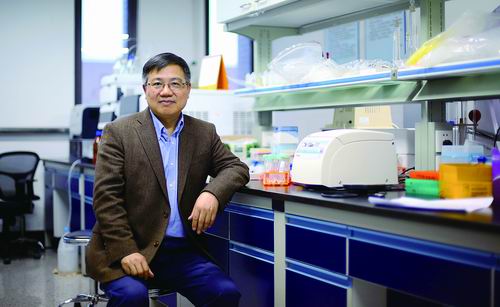
刘明耀 受访者供图
■本报见习记者 江庆龄
日前,上海邦耀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邦耀生物)宣布完成近2亿元人民币B+轮融资。这笔钱的注入让邦耀生物创始人、华东师范大学生命医学研究所所长、上海市调控生物学重点实验室主任刘明耀松了一口气。因为公司的几款新产品又能够向临床推进了,其中一款是有2024年“明星药”之称的异体通用型CAR-T细胞TyU19。
作为一种革命性的癌症治疗手段,CAR-T细胞治疗无疑是让患者“又爱又恨”的存在。该疗法在带给患者生命希望的同时,也让他们被动辄上百万元一针的价格“劝退”。其根源在于,已有的CAR-T细胞是独家定制的“一次性产品”,需从患者体内抽取T细胞,在体外进行“升级改造”后再输回该患者体内,中间涉及极为复杂且烦琐的工艺。
刘明耀告诉《中国科学报》:“如果一份CAR-T细胞产品可以供不同患者使用,成本自然就能大幅下降。”本着“科研成果最重要的是用于治病救人”的理念,刘明耀带领团队,将基因编辑技术与细胞治疗相结合,最终解决了异体细胞对病人的免疫攻击以及病人免疫排异两大科学问题。
“有望人人用得起”
刘明耀是国际上最早开始关注并使用基因编辑技术的学者之一。2012年6月,詹妮弗·杜德纳和埃马纽埃尔·沙尔庞捷关于CRISPR技术作为基因编辑工具的开创性论文发表于《科学》。14个月后,刘明耀团队就在《自然-生物技术》发表论文,成功将CRISPR-Cas9基因编辑技术应用于大鼠和小鼠的多基因同步编辑。
这项研究也为遗传疾病研究和基因治疗提供了高效的动物模型构建工具。论文上线后,刘明耀接到了很多科学家的“订单”。考虑到华东师范大学校内的实验动物平台难以满足如此大的需求,刘明耀带着十余人的团队开始创业,成立了邦耀生物,研发新型老鼠模型。
到2016年,CAR-T疗法正进入迅速发展阶段,邦耀生物也迎来了天使轮融资。此后,邦耀生物放弃了原本的动物模型业务,成为一家专注于细胞与基因治疗(CGT)的生物创新药企业。这意味着,他们需要从零开辟一条路。
尽管此前已在小鼠和大鼠中积累了大量的基因编辑技术相关经验,但刘明耀团队在试图把这套体系“搬”到人体中的过程中,依然经历了反复的失败。其中最困难的是找到人类基因组中造成异体排异的核心基因并将其敲除。
2018年,刘明耀团队做出的第一代CAR-T细胞产品在动物模型中表现良好。于是,团队第一时间同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教授张毅合作开展临床试验,但CAR-T细胞被注入志愿者体内后,很快就被排异了。
第二代、第三代、第四代……他们屡败屡战,不断缩小范围,最终找到了引发免疫排异的“罪魁祸首”,将基因特异性敲除后制备出了第六代产品BRL-303。
2024年,曙光初现。邦耀生物联合海军军医大学上海长征医院教授徐沪济的医疗团队,通过制定严密的临床方案,使用BRL-303治疗了3名患有严重复发难治性风湿免疫疾病患者,疗效显著。当年7月,这一突破性临床进展发表于《细胞》,迅速引发全球关注,并登上国内外多个重要年度榜单。
“一份异体通用型CAR-T细胞可以治疗500~1000位患者,我们估算过,等市场成熟后,治疗一位病人的成本可能不到1万元,有望人人用得起。”刘明耀告诉《中国科学报》,细胞源于健康的年轻人的血液,制备之后可保存于液氮罐中,患者可随时使用,而无须经历漫长的等待和停药时间,也避免了可能的细胞因子风暴等不安全因素。
“异体通用型CAR-T细胞对于治疗血液瘤、实体瘤以及自身免疫病都非常有潜力。”刘明耀透露,邦耀生物正在全力申报中美的临床试验批件,加速BRL-303 UCAR-T产品的上市进程。
“一生只为做药”
在过去的十余年时间里,刘明耀一共创立了3家企业,分别对应着实验室的3个研究方向,邦耀生物聚焦细胞与基因治疗,2019年成立的上海祥耀生物科技有限责任公司聚焦抗体等蛋白药物的研发,2020年成立的上海宇耀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则专注于研发小分子靶向药。
3家公司均以刘明耀名字中的“耀”命名,又与“药”谐音。“好像我生来就是做药的,一生只为做药这事而来。”刘明耀笑道。但事实上,刘明耀找到“做药”这一人生目标,确实花费了不少时间。
1982年,刘明耀从湖南师范大学本科毕业后留校读研,其间发表了不少蜘蛛行为和物种相关的论文。硕士毕业后,刘明耀在导师的建议下,前往美国继续求学,研究方向也经历了动物行为学到神经生物学,再到细胞生物学的转变。在刘明耀看来,早期“敢换专业”“敢闯入新领域”的经历,使他的视野更为开阔,并逐步建立起不同分支学科之间交叉融合的理念。
在美国加州理工学院从事博士后研究时,刘明耀师从梅尔文·西蒙。西蒙先后创立2家生物技术公司,其中Agouron Pharmaceuticals是全球首个研制出HIV蛋白酶抑制剂Viracept的公司。“我刚加入实验室时,公司的股票每股大概是4美元,博士后出站的时候已经是120美元了。”刘明耀回忆道。
同时,加州理工学院的创业氛围十分浓厚,从教授到学生,都十分推崇“下海”,学校也专门开设免费课程,普及企业管理、商业计划书撰写等商业知识。刘明耀时常出现在这些课堂上,逐渐在心中埋下了创业的种子。
2007年春节刚过,刘明耀就放弃了美国得州农工大学终身教授的职位,选择回国,从零开始筹建华东师范大学生命医学研究所。2020年,刘明耀卸任华东师范大学生命科学学院院长,专心致力于推动科研成果向临床应用转化。
“我做了一辈子基础研究,是时候往新方向努力了。”刘明耀说,“做生命医学研究,只有把科研成果用于治病救人,才能释放出科研的最大价值。”
“三五年内做出创新药”
“基础研究和产业应用之间是相辅相成的。”刘明耀解释,“实验室的原始创新成果是一家科技企业的根基,而参与成果转化的过程,又能让擅长自由探索的科学家对产业应用有着更系统和全面的认识,从实践中发掘更多‘真’问题。”
然而,要做一个有用的产品远比写论文难,做一款安全有效的原创新药,更是难上加难。“我们目前比较有代表性的几款产品,无一不是经历了5年以上的研发周期,才在临床上有一定进展。”刘明耀感慨道,“每当看到我们的产品真的能够和死神抢人,让病人恢复健康,且高质量地继续生活,就觉得所有坚持都是值得的。”
在和死神“作战”的十几年里,刘明耀也在努力让自己变得更像一位企业家。如今让刘明耀最苦恼的,还是“没钱”。在公司发展最困难的阶段,他一度抵押了自己的房子,用于支付员工的工资。支撑他走下去的,除了治病救人的理想,还有对团队和公司产品的信心。
刘明耀认为,CGT目前仍处于早期阶段,因此资本会更为谨慎。但可以确定的是,CGT将在下一个10年迎来蓬勃发展,实现突破性进展。“事实上,已经有很多资本看到了我们的潜力而持续跟投。我们也希望能够在三五年内,研发出更安全、更有效、更可及的创新药。在这之前,我们无比期待‘耐心资本’‘长期资本’的注入和创新药政策支持,加速我们的研发工作和产品开发进程。”
更让刘明耀欣慰的是,包括他们团队在内,中国生物医药领域近年来涌现出一批优秀的年轻科学家。“未来随着这些年轻人的成长,生物医药领域将迎来革命性的重大突破。”
《中国科学报》 (2025-04-07 第4版 科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