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整100年前,1925年7月,王国维在清华学校作题为《最近二三十年中中国新发见之学问》的讲演,提出“古来新学问起,大都由于新发见”的著名论断。百年来,出土简帛文献不断发现,已促成简帛学这一“新学问”的发展。到目前为止,全国各地发现的简牍总量约30万枚,帛书已发现数十件之多。早在1993年,历史学家李学勤即指出:“简帛书籍的大量涌现,正在改变古代学术史的面貌,影响甚为深远。”有关简帛研究的专著和论文不断涌现,成果丰硕。
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教授刘国忠的著作《简帛有声:出土简帛的文献学研究》(以下简称《简帛有声》)称得上是一部简帛学研究领域的前沿性成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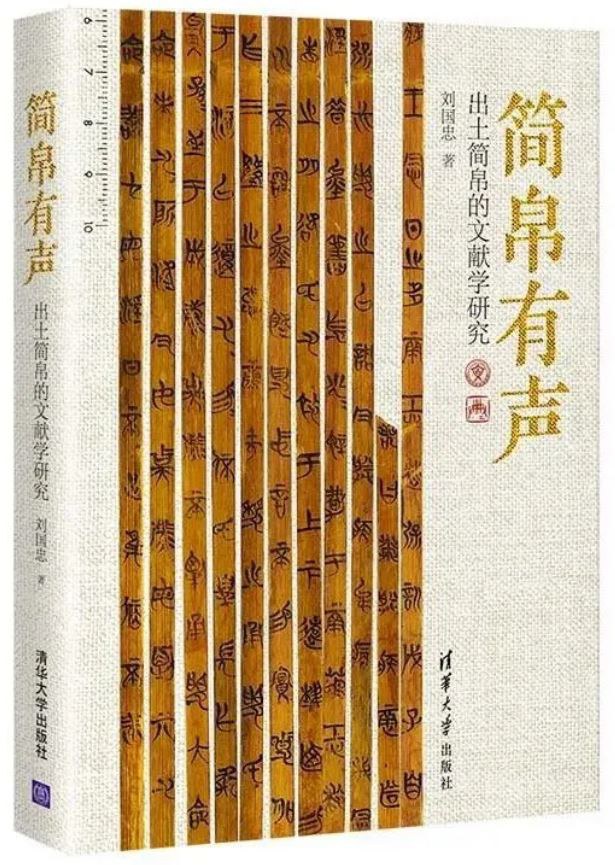 《简帛有声:出土简帛的文献学研究》,刘国忠著,清华大学出版社2024年5月出版,定价:138元。(出版社供图)
《简帛有声:出土简帛的文献学研究》,刘国忠著,清华大学出版社2024年5月出版,定价:138元。(出版社供图)
?
刘国忠于1999年撰写了首篇有关简帛文献的论文《马王堆帛书〈刑德〉乙篇再探》,之后他又先后参与清华简、长沙五一广场简的整理工作。至今,刘国忠已在简帛研究领域深耕25年,其治学立足简帛文献,注重多学科交叉研究,将微观考证与理论思考相结合。
本书共收录43篇文章,主要涉及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马王堆汉墓帛书、长沙五一广场东汉简等简帛文献的研究。书中深入浅出地探讨了出土简帛所反映的重大历史事件,如“文王称王”“武王受命”“周公居东”等命题。
《中庸》“武王末受命”句向来难解,而关键在如何训释“末”字。历来学者大致持两种意见。郑玄、孔颖达等学者将“末”理解为“老”,这是主流观点。有学者则将“末”读为“无”,或读为“未”,或为“未”的误字,即武王没有受命。这两种观点均有扞格难解之处。刘国忠在《据清华简释〈中庸〉“武王末受命”》一文中,根据清华简《保训》《程寤》《四告》等文献,尽可能还原周人眼中“文王受命”的真实内涵,即周武王继承文王开创的基业而取得克殷的胜利。至于《中庸》“武王末受命”中的“末”,应理解为“最终”,即武王最终接受了天命。刘国忠此种训释也有相关书证,他引《尚书·召诰》“王末有成命”,蔡沈即将“末”训为“终”。如此,《中庸》“武王末受命”句的理解圆通无碍,该文读来酣畅淋漓,令人茅塞顿开。
书中类似文章还有多篇,均为对传世经典文本作的微观考证。更重要的是,刘国忠还着眼于中国古代文明史与学术史的重要课题,在书中特别注重利用出土简帛文献,辨析相关史料,揭示被遮蔽的历史。
例如,在西周史领域,刘国忠关注了文王受命与称王两个问题。“文王受命”在古籍中多有记述,但该事件的具体过程在古籍中有不同说法,特别是汉代纬书中相关记述更是离奇荒诞,令人难以信服。《清华简〈程寤〉与“文王受命”》一文中提出,所谓“文王受命”,“其依据很可能正是太姒所描述的这一梦境以及相关的占测结果”。此种推论丰富了我们对“文王受命”的认识,现在已得到学界较为广泛的认同。
刘国忠还深入探讨清华简《保训》“惟王五十年”的史学价值,明确指出周文王在即位之初就已称王,且可确认其在位年数为50年,这对重新审视周文王时期商、周关系有较大帮助。此外,他还通过分析清华简《金縢》“周公宅东三年,祸人乃斯得”的记述,检视“周公居东”学术史问题,肯定了伪孔传等把周公居东解释为“周公东征”的传统观点。
立足简帛文献,既重新审视重大学术问题,也关注数术文献、行政文书,探讨以往被遮蔽的思想文化史以及基层日常行政管理等诸多问题。可以说,书中呈现出了简帛文献中多彩斑斓的历史世界。加之刘国忠深入浅出的论述、简洁晓畅的文笔,在繁杂的历史中抽丝剥茧,让读者在轻松的阅读过程中领略简帛文献的魅力。
100多年来,简帛文献的发现与研究是中华文明历史传承研究中的重要环节。如今,简帛学已成为国际性的显学。它不仅提供了新的材料,更重要的是打破了不同学科之间的壁垒,用新的理论、新的观点与新的方法,推动不同研究领域走向融合,搭建东西文化交流的桥梁。
但是,相较于实证研究,简帛学在研究对象、基本概念、学科体系等基本理论问题方面尚需加强。目前,学界已注重加强对简帛学的理论建设。同时,国内学界不断加强与国外相关领域学者的交流与合作。刘国忠也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对于简帛学建设的几点思考》一文中,他结合清华简的研究与保护经验,对简帛文献保护与整理工作展开了深入的理论思考。
这部著作体现出来的研究视野、研究方法与理论关怀,无疑将推动简帛学研究走向深处,刷新我们对中国古代文明的认知。
(作者孙进系烟台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副教授,刘子珍系贵州师范大学历史与政治学院讲师)
版权声明:凡本网注明“来源:中国科学报、科学网、科学新闻杂志”的所有作品,网站转载,请在正文上方注明来源和作者,且不得对内容作实质性改动;微信公众号、头条号等新媒体平台,转载请联系授权。邮箱:shouquan@stimes.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