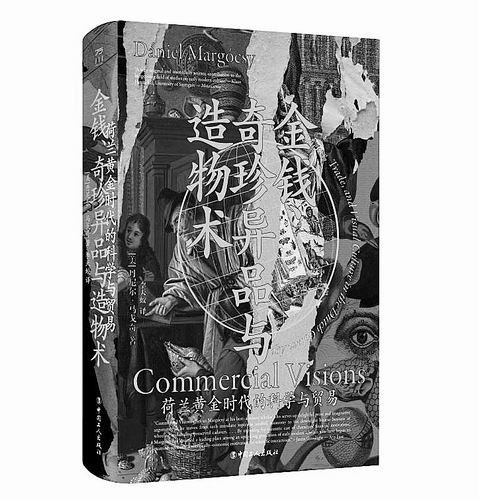 《金钱、奇珍异品与造物术:荷兰黄金时代的科学与贸易》,[美]丹尼尔·马戈奇著,李天蛟译,中国工人出版社2024年4月出版
《金钱、奇珍异品与造物术:荷兰黄金时代的科学与贸易》,[美]丹尼尔·马戈奇著,李天蛟译,中国工人出版社2024年4月出版
■ 吴燕
1710年,来自法兰克福的旅行者、藏书家和手稿收藏家扎哈里亚斯·康拉德·冯·乌芬巴赫男爵抵达阿姆斯特丹,开始了他在荷兰的旅居生活。乌芬巴赫男爵最关心的是古董和艺术品,以及博物学。
在17和18世纪,博物学已然成为一门显学。大航海时代让欧洲人可以抵达越来越远的地方,来自异域的物种与见闻是富有的收藏家们津津乐道的话题,围绕这些鲜活藏品展开的知识传播也成为那个时代知识传播中最活跃的一个领域。荷兰当然也不例外,彼时的荷兰是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有自由的空气、繁荣的经济以及活跃的跨国贸易打底,科学文化生机勃勃是水到渠成的事。
《金钱、奇珍异品与造物术:荷兰黄金时代的科学与贸易》一书所写的就是彼时彼处的智力活动与知识传播,作者丹尼尔·马戈奇是美国学者、哈佛大学的科学史博士,研究方向是现代早期科学、医学和技术的文化史。这一专业背景使他在回望历史时并不仅仅将眼光锁定在科学知识上,还将其重新置于其所处的社会文化背景之中,尤其值得称道的是他将商业维度引入这一时期欧洲博物学史中,考察了知识交流行为的商业导向。
该书以乌芬巴赫男爵的观察为主要线索,呈现了彼时彼地的博物学家群体及其博物学实践,让读者跟着男爵的脚步一路走一路看,近距离打量那个遥远年代。
一
抵达荷兰后不久,男爵便和其他外国游客一起在导游的带领下参观了莱顿的解剖演讲厅,但看来体验并不怎么好,因为导游似乎只是引领观众走马观花、浅尝辄止,所以乌芬巴赫又付费订了一次私人游览。此次虽然得见各类藏品的细节,但实际藏品却又和展览目录有些许出入,比如某些藏品被荷兰莱顿大学的解剖学教授比德洛放到了自己家中“供自己那些付费学生使用,没有面向大众进行展示”。两次参观让男爵约略感受到公共科学中的商业气息。不过在博物学家们建立各自的知识大厦的实践中,这种商业气息始终萦绕其间,成为助推知识交流的力量。
一个明显的事实是,彼时由商人打造的贸易路线、通信系统以及金融基础设施为远距离的科学知识交流奠定了物质基础,“尽管运费高昂,但是那些价格不菲的奇珍异品和博物学图册的流通量仍然获得了增长。18世纪初,很多科学产品已经变为商品,人们在世界范围内通过交易这些商品获得了利润”。不仅如此,商业还塑造了科学研究的开展方式,比如对分类学的影响就是一例。
通过商业活动,收藏家与同行或同好们的交流及藏品交换是他们丰富自己的珍奇柜以及知识的重要方式,而博物学图册和百科全书就是他们相互之间交流的重要媒介。在今天看来,这些出版物是人们了解那个时代博物学知识与实践的重要文本;但将它们置于所处时代就会发现,它们更像是收藏家们用于交易的藏品名录,博物学家会简要描述所拥有物种或标本的形态及特征,从而让其他博物学家或收藏家们借此了解其中是否有感兴趣的商品。
这就意味着商业活动,尤其是长途贸易活动的兴起成为博物学家们对物种进行识别与分类的重要因素之一。唯其如此,他们才能在相互交流时明确他们所谈论的是不是同一个物种。
在此书中,对郁金香品种的辨别就是商业因素影响科学研究实践的一个个案。早在17世纪早期,荷兰的园艺家就培育出了几十种郁金香,但是由于不同品种的价格差别很大,因此如何辨别郁金香就成为客户们急需掌握的大学问。为此,荷兰画家兼商人伊曼纽尔·斯威茨在1612年出版了一部《群芳谱》。它其实是一部广告目录,其中收录了斯威茨在法兰克福展会上要出售的郁金香。在世界各地的博物学家和商人们尚未建立一种通用的植物分类体系的时代,斯威茨的目录无疑带来了一种交易的确定性。而这件事本身也成为博物学与植物贸易相互促进、合作共赢的早期典范。
二
商业还塑造了知识传播与流通的方式。早在现代人体解剖学奠基人安德烈·维萨里的年代,医学院已开始利用解剖向学生展示人体结构。而维萨里供职过的意大利帕多瓦大学更是在1594年就启用了第一间专门用于解剖学的教室,从而使所有上课学生都能更清楚地观察尸体的解剖过程。
当乌芬巴赫男爵旅居荷兰时,解剖走出了医学院,在公众中极受欢迎。但正像马戈奇所提醒的,它对于教育和研究所起到的作用十分有限。因为这些活动通常是针对游客的付费娱乐活动,游客不但无法在活动过程中探讨问题,而且只能坐在教授和官员的后面,在很远的距离之外观察解剖台。
相比之下,人体标本和印刷图册更有利于传播与人体相关的知识。它们在17和18世纪的荷兰也形成了竞争,两种方法的代表人物都是当时著名的解剖学家:勒伊斯专注于人体标本制作,而比德洛则对印刷图册情有独钟。假如这老哥儿俩联袂,多半会成就一段学术互助的佳话。不过,他们虽在各自的方向上都是一等一的人物,但两个人之间并不怎么对付,这在很大程度上缘于他们之间存在商业竞争。
先说勒伊斯。在他看来,蜡注射标本的优点在于能够提供关于人体的确凿证据,而且可以反复检查。所以他一生专注于人体标本的制作,并发展出了一套技术,从而使标本制作达到很高的水平。
他最著名的客户就是彼得大帝。他不但将精心制备的藏品卖给彼得大帝,还以5000荷兰盾的价格向彼得大帝出售了“只有他本人掌握”的标本制作方法。将制作方法写下来出售而不是亲赴圣彼得堡以师傅带学徒的方式传授技艺,这当然是勒伊斯为维护自己的知识产权而作出的聪明选择。
但如果深究一下我们也会发现,当勒伊斯将自己的制备方法写下来的时候,他在制作人体标本这件事上已经不再只是一个掌握某种技术的手艺者,还是一位具有现代色彩的知识传播者。相比于手把手口传心授,制备方法的撰写与解读无疑都需要更多特殊的理论知识,比如有关定量、配比的知识。而促使他实现这一转型的依然是对商业利益的考量。
再说比德洛,作为与勒伊斯同时代的另一位著名解剖学家,比德洛教授对勒伊斯的标本呈现方式并不认同。他认为注蜡会扩张血管,勒伊斯的方法在标本制作过程中引入了人为因素,这并不利于准确表现人体的自然形态。比德洛更认同的方式是图册,并且认为只有图像才能更为理性地重现人体的真实面貌。他的《人体解剖学》出版于1685年,并迅速成为那个时代欧洲价格最高但仍大受欢迎的插图百科全书之一。
在勒伊斯看来,印刷出版物只是对标本进行传播推广的媒介;而对比德洛来说,书籍才是展现人体的终极商品。不难看出,同为17世纪成就卓越的解剖学家,勒伊斯和比德洛在上述认识上的分歧同样包含着商业上的考量。两位大咖终其一生也未能化解的分歧,也是商业竞争的一种表现形式。
本书作者马戈奇分析到,比德洛对勒伊斯的标本制作方法大加抨击,原因在于比德洛希望通过贬低与其形成竞争关系的标本这一表现媒介来推广自己的图册。
勒伊斯与比德洛在认识上的分歧在当时并非孤例。根据马戈奇的观察,彼时的博物学家们彼此相识,有许多合作,但“他们之间并不总是存在良好的个人关系。他们会相互竞争,争夺乌芬巴赫这样的客户”。
不过,与很多人的见解不同,马戈奇认为这种基于各自商业利益而形成的科学争论,比如勒伊斯和比德洛在人体构造的视觉呈现方式上的分歧,其实并不是什么坏事,因为他们在竞争中所抱持的科学观点和哲学观点在今天仍然会促使人们根据图像、标本以及其他视觉呈现形式做出深刻的哲学思考。
因此,马戈奇评论说:“与集中研究科学知识如何日趋稳定的过程相比,历史学家或许更应该关注科学知识的商品化过程与争论情况。随着知识在几百年里的积累,所有的科学共识最终都会被推翻。但有关哲学观点以及这些观点赋予的动态商业情境将反复出现。现代科学事业的核心是分歧,而非共识。”
至此,有关荷兰黄金时代科学与贸易图景的重现已经走向了对方法论的追问。每个时代的知识大厦日趋稳定来自共识,而知识的更新则来自每一次共识的打破,它可能表现为某种争论或竞争,而无论是什么力量促使变化的发生,对其的探索都将是令人着迷的智力活动,因为由此呈现出的将是一部充满生机的知识史,一部有人并且因为有人而鲜活的历史。
(作者系内蒙古师范大学科学技术史研究院教授)
《中国科学报》(2024-12-13第3版读书)
特别声明:本文转载仅仅是出于传播信息的需要,并不意味着代表本网站观点或证实其内容的真实性;如其他媒体、网站或个人从本网站转载使用,须保留本网站注明的“来源”,并自负版权等法律责任;作者如果不希望被转载或者联系转载稿费等事宜,请与我们接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