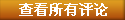|
|
|
|
|
гҖҗ科еӯҰж—¶жҠҘгҖ‘иў«вҖңз–ҸиҝңвҖқзҡ„д№Ұйҷў |
|
|

з«ҜеҚҲиҠӮжңҹй—ҙпјҢ笔иҖ…еҲ°еұұиҘҝзҺ©гҖӮдёүжҷӢеӨ§ең°жІҗжөҙеңЁеҲқеӨҸзҡ„е’ҢйЈҺз»ҶйӣЁд№ӢдёӯгҖӮй•ҝжңҹд»ҘжқҘпјҢй«ҳиҖёзҡ„еӨӘиЎҢеұұе’Ңеҗ•жўҒеұұдёҖе®ҡзЁӢеәҰдёҠеңЁдёңиҘҝдёӨйқўйҳ»йҡ”дәҶдәәеҸЈжөҒеҠЁе’Ңзү©иө„еҫҖжқҘпјҢдҪҝеҫ—еұұиҘҝжҲҗдёәдёӯеӣҪеҢ—ж–№зҡ„дёҖдёӘ“ејӮеҹҹ”пјҢж–№иЁҖгҖҒд№ дҝ—гҖҒж–Үзү©дҝқз•ҷеҫ—зӣёеҜ№е®Ңж•ҙгҖӮ
еңЁеұұиҘҝжҰҶж¬ЎпјҢ笔иҖ…еҸӮи§ӮдәҶ“еҮӨйёЈд№Ұйҷў”гҖӮжҰҶж¬ЎеҮӨйёЈд№ҰйҷўжҳҜжё…д»ЈжҰҶж¬ЎеҺҝеӯҰпјҢжҳҜеҸӨд»ЈеұұиҘҝжҰҶж¬Ўзҡ„жңҖй«ҳеӯҰеәңгҖӮд№ҫйҡҶдёүеҚҒдёҖе№ҙпјҲ1766е№ҙпјүз§°еҮӨйёЈд№ҰйҷўпјҢеҚ ең°2700е№іж–№зұіпјҢе‘Ҳеӣӯжһ—ејҸеёғеұҖпјҢиҷҪ然жҳҜиҝ‘е№ҙжқҘжҢүз…§еҸӨд»Је»әзӯ‘ж јеұҖж—§еқҖзҡ„еӨҚе»әпјҢдҪҶд№ҹиғҪеӨҹзңӢеҲ°еҪ“е№ҙд№Ұйҷўзҡ„зӣӣеҶөгҖӮ
еӣһзЁӢзҡ„и·ҜдёҠпјҢйҖ”з»ҸеұұиҘҝиҙўз»ҸеӨ§еӯҰжҰҶж¬Ўж ЎеҢәпјҢзҺ°д»Је»әзӯ‘жһ—з«ӢгҖӮжғіеҸҠеҜҘиҗҪзҡ„“еҮӨйёЈд№Ұйҷў”пјҢд»Ҡжҳ”еҜ№жҜ”еҲҶжҳҺгҖӮеҗҢдёәдј жүҝдәәзұ»ж–ҮжҳҺгҖҒеҲӣйҖ зҹҘиҜҶгҖҒеҹ№е…»дәәжүҚзҡ„жңәжһ„пјҢдёәд»Җд№ҲеңЁдёӨиҖ…д№Ӣй—ҙжңүеҰӮжӯӨзҡ„йёҝжІҹпјҹ
жғіиө·жңүзқҖ800е№ҙж ЎеҸІзҡ„еү‘жЎҘзүӣжҙҘпјҢжңүзқҖиҝ‘400е№ҙж ЎеҸІзҡ„е“ҲдҪӣпјҢдёӯеӣҪзҺ°д»ЈеӨ§еӯҰе’ҢдёӯеӣҪеҸӨд»Јд№Ұйҷўд№Ӣй—ҙпјҢдјјд№ҺжІЎжңүд»»дҪ•еҶ…еңЁзҡ„е…іиҒ”——жҲ‘们зҡ„зҺ°д»ЈеӨ§еӯҰйҮҢйқўжІЎжңүжңүеҗҚжңүеҸ·зҡ„е»әзӯ‘жқҘж ҮжҰңеӨ§еӯҰзҡ„еҸӨиҖҒпјҢзЁҖиҗҪзҡ„еҸӨд»Јд№ҰйҷўйҒ—иҝ№дёӯжІЎжңүйқ’жҳҘзҡ„иә«еҪұе’Ңжң—жң—зҡ„иҜ»д№ҰеЈ°гҖӮ
дёҖеҚғеӨҡе№ҙзҡ„д№Ұйҷўдёәд»Җд№ҲжІЎжңүеңЁ“дёӯеӯҰдёәдҪ“гҖҒиҘҝеӯҰдёәз”Ё”зҡ„иҝ‘д»ЈдёӯеӣҪе®ҢжҲҗиҪ¬еһӢжҲҗдёәзҺ°д»ЈеӨ§еӯҰпјҢиҖҢеңЁж»ҡж»ҡдёңжқҘзҡ„иҘҝеӯҰеӨ§жҪ®йқўеүҚжҖҘжөҒеӢҮйҖҖпјҹжҲ–и®ёпјҢиҝҷдёҺд№Ұйҷўж•ҷиӮІзҡ„еҶ…е®№дё»дҪ“е’ҢиҘҝеӯҰзҡ„е·ЁеӨ§е·®ејӮжңүе…іпјҢд№ҹдёҺд№Ұйҷўж•ҷиӮІзҡ„еҠһеӯҰдё»дҪ“еӨ§еӨҡжқҘиҮӘж°‘й—ҙе’Ңең°ж–№жңүе…іпјҢжӣҙдёҺдёӯеӣҪиҝ‘д»Јд»ҘжқҘжҝҖиҚЎеңЁзӨҫдјҡеҗ„дёӘйўҶеҹҹзҡ„жҺЁеҖ’йҮҚжқҘзҡ„йқ©е‘ҪйҖ»иҫ‘жңүе…ігҖӮ
19дё–зәӘеҗҺжңҹпјҢдёӯеӣҪзҹҘиҜҶеҲҶеӯҗеңЁд№ҰйҷўеҺ»з•ҷиҝҷдёҖй—®йўҳдёҠпјҢжӣҫжңүзқҖе·ЁеӨ§дәүи®®гҖӮеәҹ科дёҫпјҢејҖеӯҰе ӮпјҢиӮІдәәжүҚ——иҝҷеҮ д№ҺжҳҜжҷҡжё…еҝ—еЈ«зҡ„е…ұеҗҢзңӢжі•пјҢиҖҢ他们д№Ӣй—ҙзҡ„еҲҶжӯ§еңЁдәҺе…·дҪ“зӯ–з•ҘпјҢе°Өе…¶жҳҜеҰӮдҪ•зңӢеҫ…жәҗиҝңжөҒй•ҝзҡ„д№ҰйҷўгҖӮ“ж—¶еұҖеӨҡиү°пјҢйңҖжқҗе°ӨжҖҘ”пјҢж— жі•з”ҹдә§еқҡиҲ№еҲ©зӮ®гҖҒеҹ№е…»з§‘жҠҖдәәжүҚзҡ„д№ҰйҷўпјҢе…¶ж•ҷеӯҰе®—ж—ЁеҸҠеҹ№е…»ж–№жЎҲпјҢйқһж”№дёҚеҸҜгҖӮдәҺжҳҜпјҢеҮәзҺ°дәҶдёүз§ҚйўҮжңүе·®ејӮзҡ„йҖүжӢ©пјҢдёҖжҳҜж•ҙйЎҝд№ҰйҷўпјҢеўһеҠ иҘҝеӯҰиҜҫзЁӢпјӣдәҢжҳҜдҝқз•ҷд№ҰйҷўпјҢеҸҰеӨ–еҲӣи®ҫи®ІжұӮе®һеӯҰзҡ„ж–°ејҸд№ҰйҷўжҲ–еӯҰе ӮпјӣдёүжҳҜиҜ·зҡҮдёҠеҸ‘еёғиҜҸд№ҰпјҢ“е°Ҷе…¬з§ҒзҺ°жңүд№Ӣд№ҰйҷўгҖҒд№үеӯҰгҖҒзӨҫеӯҰгҖҒеӯҰеЎҫпјҢзҡҶж”№дёәе…јд№ дёӯиҘҝд№ӢеӯҰж Ў”гҖӮ1901е№ҙжё…ж”ҝеәңдёӢиҜҸ“еҗ„зңҒжүҖжңүд№ҰйҷўдәҺзңҒеҹҺеқҮж”№и®ҫеӨ§еӯҰе Ӯ”пјҢж Үеҝ—зқҖе®һиЎҢдәҶдёҖеҚғеӨҡе№ҙзҡ„д№ҰйҷўеҲ¶еәҰеҹәжң¬йҖҖеҮәеҺҶеҸІиҲһеҸ°пјҢеӣӣе№ҙеҗҺзҡ„1905е№ҙпјҢ科дёҫеҲ¶еәҰеәҹжӯўпјҢеҪўжҲҗж–°ејҸеӯҰе ӮдёҖз»ҹеӨ©дёӢзҡ„еұҖйқўпјҢжӯӨеҗҺпјҢд№ҰйҷўеҲ¶еәҰе’Ңд№ҰйҷўзІҫзҘһйҷ·е…Ҙй•ҝжңҹзҡ„жІүеҜӮгҖӮеҸ–ж¶Ҳд№ҰйҷўпјҢд»ҘдҫҝйӣҶдёӯдәәеҠӣиҙўеҠӣпјҢеҸ‘еұ•ж–°ж•ҷиӮІпјҢиҝҷдёҖ“е…ҙеӯҰиҮійҖҹд№Ӣжі•”з»ҲдәҺжҲҗдёәжңҖй«ҳз»ҹжІ»иҖ…зҡ„и°•д»ӨпјҢйҖҡиЎҢе…ЁеӣҪгҖӮ
д№Ұйҷўж•ҷиӮІзҡ„зү№зӮ№пјҢеңЁж•ҷиӮІжЁЎејҸдёҠжҳҜдёӘдҪ“дёҺдёӘдҪ“д№Ӣй—ҙзҡ„дәӨжөҒпјҢеңЁж•ҷеӯҰеҶ…е®№дёҠжҳҜеҝғжҖ§дҝ®е…»зҡ„е®Ңе–„пјҢеңЁж•ҷиӮІеҲ¶еәҰдёҠжҳҜж°‘й—ҙиҮӘдё»дёҺе®ҳж–№з®ЎеҲ¶зҡ„з»“еҗҲгҖӮиғЎйҖӮжӣҫиҜҙпјҢ“д№ҰйҷўжҳҜдёӯеӣҪдёҖеҚғе№ҙжқҘйҖҗжёҗжј”еҢ–еҮәжқҘзҡ„дёҖз§Қй«ҳзӯүж•ҷиӮІеҲ¶еәҰ”гҖӮе®ғе’ҢеӯҰж Ўзҡ„жңҖеӨ§еҢәеҲ«пјҢе°ұеңЁдәҺеүҚиҖ…жіЁйҮҚиҮӘдҝ®пјҢеҗҺиҖ…жіЁйҮҚи®ІжҺҲпјӣеүҚиҖ…жҸҗеҖЎиҮӘеҠЁең°з ”究пјҢеҗҺиҖ…еҘүиЎҢ“иў«еҠЁең°жіЁе°„”гҖӮз« еӨӘзӮҺжҢҮеҮәпјҡеҪ“е№ҙд»ҘеӯҰж ЎеҸ–д»Јд№ҰйҷўпјҢеҫҲе®№жҳ“еҜјиҮҙж°‘й—ҙеӯҰжңҜзҡ„иҗҺзј©пјҢиҝӣиҖҢеүҘеӨәдәә们著д№Ұз«ӢиҜҙгҖҒж Үж–°з«ӢејӮзҡ„жқғеҲ©гҖӮ
ж—©еңЁ1925е№ҙпјҢз•ҷзҫҺеҪ’жқҘзҡ„йҷҲе“ІиЎЎгҖҒд»»йёҝйҡҪе°ұдё»еј е°Ҷ欧зҫҺиҜёеӣҪзҡ„еӨ§еӯҰеҲ¶еәҰдёҺдёӯеӣҪдј з»ҹзҡ„д№ҰйҷўзІҫзҘһеҗҲдәҢдёәдёҖпјҢиҝҷдёҺжё…еҚҺж Ўй•ҝжў…иҙ»зҗҰгҖҠеӨ§еӯҰдёҖи§ЈгҖӢдёӯзҡ„иҜҙжі•дёҚи°ӢиҖҢеҗҲгҖӮз ”з©¶иҖ…и®ӨдёәпјҢдёӯеӣҪзҡ„еӨ§еӯҰж•ҷиӮІеңЁеҖҹйүҙ欧зҫҺзҺ°д»ЈеӨ§еӯҰеҲ¶еәҰзҡ„еүҚжҸҗдёӢпјҢеә”иҜҘд»ҺдёүдёӘж–№йқўжҢ–жҺҳдј з»ҹд№ҰйҷўеҲ¶еәҰзҡ„зҺ°д»Јд»·еҖјпјҡж•ҷиӮІдҪ“еҲ¶ж–№йқўпјҢеә”иҖғиҷ‘з§Ғз«ӢеӨ§еӯҰе’Ңж°‘й—ҙеӯҰдјҡзҡ„иҙЎзҢ®пјӣж•ҷиӮІзҗҶеҝөж–№йқўпјҢеә”йҮҚи§Ҷе…Ёдәәж јж•ҷиӮІгҖҒйҖҡиҜҶж•ҷиӮІе№¶жү“з ҙж•ҷиӮІзҡ„е®һз”Ёдё»д№үдј з»ҹпјӣж•ҷеӯҰж–№жі•ж–№йқўпјҢеә”жіЁйҮҚеӯҰз”ҹзҡ„иҮӘдё»еӯҰд№ е’ҢеёҲз”ҹд№Ӣй—ҙзҡ„дә’еҠЁгҖӮж— з–‘пјҢдёҠиҝ°дёүдёӘж–№йқўеҜ№д»ҠеӨ©зҡ„й«ҳзӯүж•ҷиӮІж”№йқ©жқҘиҜҙжҳҫ然жҳҜйҡҫиғҪеҸҜиҙөзҡ„гҖӮ
дҪҶжҳҜпјҢиҝҷз§ҚеҜ№дёӯеӣҪеӨ§еӯҰж”№йҖ зҡ„зҗҶжғіе№¶жңӘеҫ—д»ҘзңҹжӯЈе®һи·өгҖӮж—¶иҮід»Ҡж—ҘпјҢд№Ұйҷўж•ҷиӮІзҡ„зҺ°д»Јж„Ҹд№үд»Қ然жңӘеҸ—еҲ°е№ҝжіӣйҮҚи§ҶгҖӮд№Ұйҷўзҡ„зІҫзҘһе·Із»ҸиҝңеҺ»гҖӮеӨ§еӯҰзҡ„ж•ҷиӮІжЁЎејҸгҖҒж•ҷеӯҰеҶ…е®№гҖҒеҹ№е…»зӣ®ж ҮпјҢдёҺдј з»ҹд№Ұйҷўж јж јдёҚе…ҘгҖӮиҝ‘е№ҙжқҘиҷҪжңүеӨҡжүҖи‘—еҗҚеӨ§еӯҰиҜ•еӣҫе°Ҷд№Ұйҷўдј з»ҹеј•е…ҘзҺ°д»ЈеӨ§еӯҰпјҢдҪҶдјјд№Һж•Ҳжһң并дёҚжҳҺжҳҫпјҢжҲҗж•Ҳ并дёҚжҳҫи‘—гҖӮеӨұеҺ»д№Ұйҷўдј з»ҹзҡ„зҺ°д»ЈеӨ§еӯҰпјҢйҷӨдәҶж•ҷдјҡдәә们иө„д»Ҙз”ҹеӯҳе’Ңе·ҘдҪңзҡ„дё“дёҡжҠҖиғҪпјҢеңЁеҝғжҖ§дҝ®е…»гҖҒж–ҮеҢ–дј жүҝж–№йқўзҡ„еҠҹз”Ёе·ІеӨ§жү“жҠҳжүЈгҖӮ
д»Һжӣҙе®Ҹи§Ӯзҡ„и§ҶйҮҺжқҘзңӢпјҢд№ҰйҷўеңЁиҪ¬еһӢе№ҙд»Јзҡ„е‘ҪиҝҗдёҺжҷӢе•ҶеҸҠе…¶еұұиҘҝзҘЁеҸ·зҡ„е‘ҪиҝҗеҰӮеҮәдёҖиҫҷпјҢе®ҢжҲҗдәҶ他们еҗ„иҮӘзҡ„еҺҶеҸІдҪҝе‘ҪеҗҺйҖҖеҮәдәҶеҺҶеҸІзҡ„иҲһеҸ°пјҢдёҖзҷҫе№ҙеҗҺзҡ„д»ҠеӨ©дҫӣдәә们еҸӮи§Ӯе’Ңи°Ҳи®әгҖӮ
жҲ‘们еҝғдёӯзҡ„зә з»“еңЁдәҺпјҢд№Ұйҷўе’ҢзҘЁеҸ·дёәд»Җд№ҲеңЁиҝ‘д»ЈдёӯеӣҪзҡ„еӨ§еҸҳйқ©дёӯж— жі•е®ҢжҲҗиҮӘиә«зҡ„зҺ°д»ЈиҪ¬еһӢпјҢиҖҢжҲҗдёәзҺ°д»ЈеӨ§еӯҰе’Ң银иЎҢжңәжһ„пјҹдёҺжӯӨзӣёе…ізҡ„еҸҰдёҖдёӘй—®йўҳжҳҜпјҢд»ҠеӨ©зҡ„еҗ„зұ»жңәжһ„пјҢеңЁдёҚж–ӯеҸҳиҝҒдёӯзҡ„зҺҜеўғпјҢиғҪеҗҰдёҺж—¶д»ЈдҝқжҢҒеҗҢжӯҘпјҹеҰӮжһңдёҚиғҪпјҢе®ғ们зҡ„е‘ҪиҝҗеҸҲе°ҶеҰӮдҪ•е‘ўпјҹ
еҪ“д№ҰйҷўйҖҗжёҗиў«“з–Ҹиҝң”并еңЁжҺЁеҖ’иҖҢеҗҺеӨҚе»әдёәзҺ°д»ЈзӨҫдјҡзҡ„ж—…жёёж –жҒҜең°ж—¶пјҢжёёе®ўжӢ–зқҖеҢҶеҝҷиҖҢз–Іжғ«зҡ„и„ҡжӯҘпјҢйҷӨдәҶеңЁ“ж–ҮжҳҢйҳҒ”дёӢе°ҸжҶ©пјҢжІЎжңүеҝғжҖқи®Өзңҹз ”иҜ»й•ҢеҲ»еңЁеўҷеЈҒдёҠзҡ„гҖҠи®әиҜӯгҖӢгҖҠеӯҹеӯҗгҖӢпјҢдәә们д№ҹдёҚеҶҚеҸҜиғҪеңЁ“и—Ҹд№ҰжҘј”дёӢй—»еҲ°д№ҰйҰҷгҖӮ
еҺҶеҸІз»ҷжҲ‘们丰еҜҢзҡ„еҗҜзӨәгҖӮжҰҶж¬ЎиҖҒеҹҺйҮҢдәәеҪұзЁҖз–Ҹзҡ„д№ҰйҷўпјҢжҳҜдёҖйқўй•ңеӯҗгҖӮ
пјҲдҪңиҖ…еҚ•дҪҚпјҡдёӯ科йҷўеҢ—дә¬еҲҶйҷўпјү
гҖҠ科еӯҰж—¶жҠҘгҖӢ (2011-06-13 A3 и§ӮеҜҹ иҜ„и®ә)